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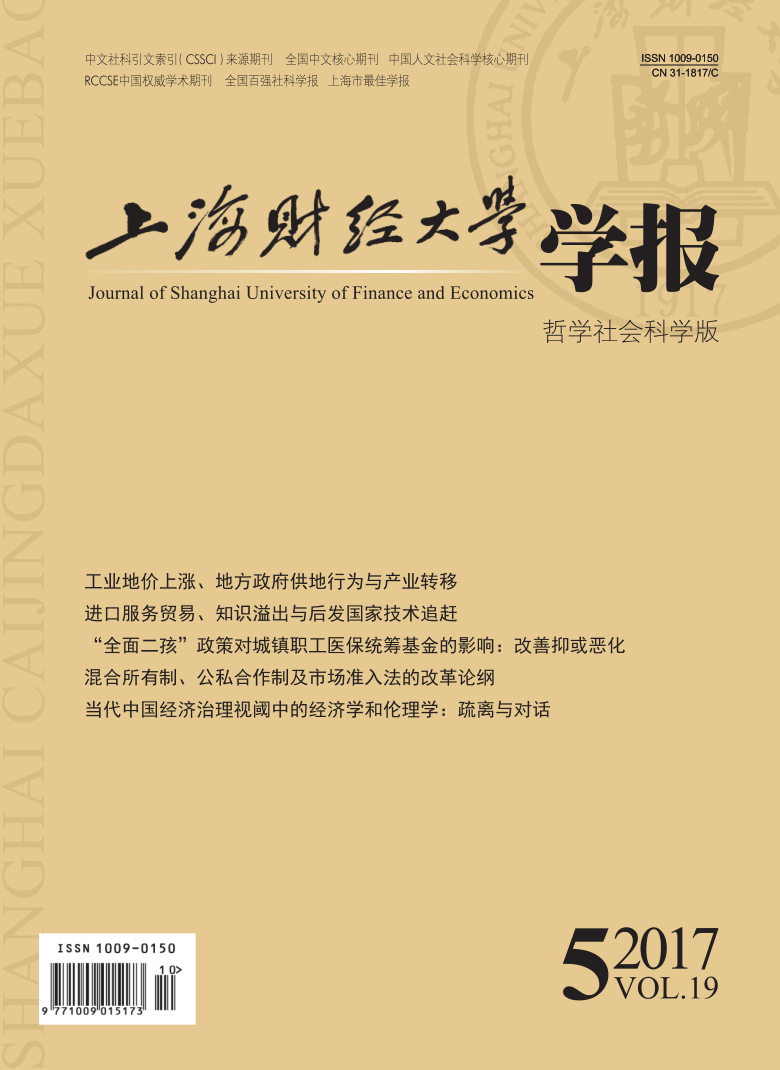 |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19卷第5期 |
- 周晖, 邓舒
- Zhou Hui, Deng Shu
- 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
-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rom a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 19(5): 27-39.
-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7, 19(5): 27-39.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7-03-22

2017第19卷第5期
2015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以及近年来“两会”期间对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节能减排等生态环保话题的关注表明,全社会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这要求企业应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管理措施,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减少污染,以承担环境责任(Hoffman,2000)。因而作为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是环境责任承担者的企业高管,必将受到来自政府和公众的制度压力与环境压力,进而对企业环境策略的实施产生影响。作为激励高管的一种方式,薪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管过去的经营业绩和管理品行,从而必然会影响高管对于当前环境绩效的行为决策。
因此,确定合理的高管薪酬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企业自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在中国的政策导向与制度背景下,外部治理环境会对企业高管行为决策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李延喜和陈克兢,2014)。现有关于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集中探讨短期、长期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对这两者关系的影响(Berrone和Gomez-Mejia,2009;Zou等,2015a),较少研究高管薪酬水平的不同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这两者关系的影响。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对公司内部治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La Porta等(1998)提出,可以将外部治理环境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中。那么高管薪酬水平的高低会对环境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呢?不同高管薪酬水平下外部治理环境会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这是现有研究缺少关注却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合法性机制,在研究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时,通过PSM方法排除内生性因素的干扰,对高管薪酬进行低水平与高水平分组,考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不同水平的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产生的影响,揭示高管薪酬是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应将环境绩效作为构建高管薪酬体系时要考虑的重要指标及考核要项。此外,本文引入外部治理环境这一变量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明晰了不同高管薪酬水平下外部治理环境对这两者关系的影响。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经验,本文主要从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外部治理环境(李延喜和陈克兢,2014)。
本文首次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声誉模型,有效地将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突破了单一的线性关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部治理环境视角下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影响的文献。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企业制定合理高管薪酬与政府营造良好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决策依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通过引言,引入研究背景,梳理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已做的工作,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就本文所做的探索性补充完善工作做了描述;其次对有关高管薪酬、环境绩效的文献做了综评;第三部分结合代理理论与合法性机制,从外部治理视角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假设说明;在第四部分进行了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与讨论;最后一部分阐释了研究结论、意义及局限性。
二、文献回顾高管薪酬因其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倍受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关于高管薪酬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早期研究中,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随着高管薪酬激励方案的多样化与设计的合理化,盛明泉和车鑫(2016)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这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于环境绩效而言,环境信息披露是影响它的一个重要变量。吕峻(2012)在基于合法性理论的研究中发现,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而Iatridis(2013)在基于自愿披露理论的研究中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沈洪涛等(2014)结合以上两种理论研究发现,企业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呈U形相关。Meng等(2014)的研究却显示,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环境信息披露不能评判环境绩效的好坏。
为了让高管积极地进行环境管理,企业会通过薪酬激励的方式,使其完成环境目标,实现利益最大化。高管薪酬的考核是基于高管以往的绩效水平,因此会影响高管下一阶段对环境的行为决策(Zou等,2015a)。所以,与高管薪酬和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类似,高管薪酬不仅会受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也会影响公司的环境绩效(Conyon和He,2011)。例如,Zou等(2015a)研究发现,企业通过高管激励的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提高环境绩效水平;吴德军和黄丹丹(2013)基于制度和代理理论,发现只有高管长期薪酬激励才对环境治理有正向影响;李平等(2015)的研究表明,公司管理激励中高管短期激励才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也有学者发现,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是负相关关系(Collett和Miles,2013)。此外,Cong和Freedman(2011)认为,高管薪酬与企业的环境治理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见,当前研究并未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达成一致。
此外,现有关于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内部属性,包括企业规模、股权结构、所属行业等因素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这两者关系的影响,而鲜有基于外部治理环境视角对这两者关系影响的研究。实际上,环境绩效的变化不仅源于内部机制,也会受外部治理环境,包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采用我国2009–2012年沪深两市166家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高管薪酬水平下外部治理环境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总之,在企业经济行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综合治理刻不容缓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本文研究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价值与实践借鉴意义。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目前关于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研究大多基于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合法性机制,考虑了不同的高管薪酬水平下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第二,与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内部属性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不同,本文通过外部治理环境从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两个层面,来研究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丰富了宏观视角下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第三,发现企业环境绩效会随着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而改善,但是在不同的高管薪酬水平下,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机理不同。因此,本文为在企业高管薪酬考核中应加入环境绩效要素这一评价指标提供了支持证据,同时为政府通过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来影响高管的管理决策行为,进而提高环境绩效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公司管理者行为与环境表现之间关系的基础。Fama(1980)提出在委托人很难验证代理人的行为时,可利用代理人的市场声誉效应来约束其行为,促使代理人尽心工作。当高管的薪酬处于较低水平时,表明在竞争市场中,其价值还未充分体现。根据代理理论的声誉模型可知,高管的市场价值取决于长期的业绩与品行,因此其必须努力工作,为企业创造价值,提升自己在高管市场中的声誉,才能提高未来的薪酬水平。随着政府、公众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因为环境投资带来的环境合法性而降低责任风险,提高企业声誉,降低融资成本,增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从中获益(Melo和Garrido-Morgado,2012)。此外,企业还可以依靠在环境保护中塑造的良好形象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凭借在环境保护中获得的主动权快速通过新产品环保认证,取得在新产品市场的先发优势。因此,薪酬水平较低的高管为了表现优异,会密切关注企业利益,关心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注重环境保护以及环境绩效管理。可见,当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企业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当高管的薪酬处于较高水平时,表明高管的价值在竞争市场中得以充分体现,其努力也会随之而递减。当公司要进行环境保护时,高管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环境策略,进行产品的重新设计、技术创新、设备匹配以及员工的再次培训等(Zou等,2015b)。在这种情况下,高管会因为环保投资具有的风险性以及精力的耗费,倾向于风险规避和不作为,不愿意提升环境绩效(Qi等,2013)。因此,高管会更容易产生自利行为,利用其职权控制公司的业务,关注个人的经济利益,来确保维持当前的薪酬水平。此外,当高管薪酬过高时,也自然挤占了一部分环保投资。可见,当高管薪酬水平较高时,企业的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
North(1990)提出,外部治理环境是规范基本社会、政治与法律中出现的有关生产、交换与分配的规则,它有利于激励人类中产生的经济或政治交易行为。政府干预作为外部治理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会对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一定的影响。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提出,政府干预可以影响企业的行为决策。当政府对企业过度干预时,企业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同时企业管理者的既得利益会被侵占,企业管理者会对政府干预加以防范,从而使政府与企业高管形成竞争与替代的关系(白俊和连立帅,2014)。由此可见,政府干预会对高管薪酬激励产生影响。Boubakri等(2008)提出的管理观点认为,政府干预会减弱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沈永建和倪婷婷(2014)的研究也发现,政府干预会使企业形成政策性负担,从而负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此外,张功富(2013)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对企业扩大环保投资与改善环境质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反而政府干预越强,企业环境绩效水平越差。同时,王耀东(2016)的研究发现,政府采用间接干预比直接干预更容易促使企业加大环保力度,优化环境质量。因此,当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高管想要表现自身的价值,获得良好的声誉,会倾向于在环境保护方面为企业创造价值,但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管激励机制的运行效果,阻碍了高管薪酬在环境绩效方面的提升。当高管薪酬水平较高时,其价值已经在竞争市场体现,此时,高管会倾向于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而规避环保投资方面的风险,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出不作为倾向。政府干预对高管激励具有替代作用,进一步遏制了高管在提升环境保护方面做出努力的可能。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低高管薪酬水平下,政府干预会弱化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H2b:高高管薪酬水平下,政府干预会强化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与政府干预一样,法治水平作为外部治理环境的一个主要要素,在解决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高管会更倾向于将其纳入公司的行为决策中(North,1981)。企业所处的地区法治水平越高,企业面临的法律、社会和公众监管压力越大,相应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也就越高。Menguc等(2010)发现,当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法治监管时,会利用强制手段严格管制企业在污染物方面的排放。Dawkins和Fraas(2011)支持这一观点,并认为这样还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同时,当法治水平越高时,企业直接面临着来自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更大压力,会更为积极地采取环保措施,以期避免环保处罚,获得在环境合法化方面的竞争优势。因此,当高管薪酬处于较低水平时,高管为了体现自己对企业的价值,当面临来自环保方面严苛的法治要求时,在严格的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会更乐于做“正确的事”,即进一步实施环保行为,提升环境绩效,以获得环境合法性。当高管薪酬处于较高水平时,高管获得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利益。在企业处于较高的法治水平环境条件下,为了避免环保风险,出现环境违规而发生的法律制裁行为,高管需要获得环境合法性,因而会进行环境保护,弱化降低环境绩效水平的动机,促使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低高管薪酬水平下,法治水平会强化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H3b:高高管薪酬水平下,法治水平会弱化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9–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初选样本,为提高数据有效性,本文通过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剔除:(1)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上市公司数据;(2)剔除ST和ST*类公司数据;(3)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在回归分析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66家公司的585个观测值。
本文数据的获取通过以下途径:(1)高管薪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2)环境绩效数据和其他企业数据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手工收集、整理、核实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获取来源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3)外部治理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樊纲等,2011)。
(二) 研究模型第一步:为了验证本文假设1中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构建了以下多元一次与二次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 $\begin{aligned}CEP = & {\beta _0} + {\beta _1}SALARY + {\beta _2}GOV + {\beta _3}LAW + {\beta _4}INDUSTRY + {\beta _5}ISO + \\& {\beta _6}SIZE + {\beta _7}NATURE + {\beta _8}MARKET + {\beta _9}ROA + {\beta _{10}}YEA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 (1) |
| $\begin{aligned}CEP = & {\beta _0} + {\beta _1}SALARY + {\beta _2}SALAR{Y^2} + {\beta _3}GOV + {\beta _4}LAW + {\beta _5}INDUSTRY + \\& {\beta _6}ISO + {\beta _7}SIZE + {\beta _8}NATURE + {\beta _9}MARKET + {\beta _{10}}ROA + {\beta _{11}}YEA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 (2) |
其中,β 0为常数项,β 1–β 11为各变量系数,ε为残差。CEP代表环境绩效,为被解释变量;SALARY为高管薪酬,为解释变量;其他为可能影响环境绩效的控制变量。
第二步:在通过模型(1)和模型(2)验证假设1的前提下,本文对高管薪酬进行分组,构建了模型(3)来检验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验证假设2和假设3。为了避免外部治理环境的两个变量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将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分别放入模型3中进行检验。
| $\begin{aligned}CEP = & {\beta _0} + {\beta _1}SALARY + {\beta _2}INS + {\beta _3}SALARY \times INS + {\beta _4}INDUSTRY + {\beta _5}ISO + \\& {\beta _6}SIZE + {\beta _7}NATURE + {\beta _8}MARKET + {\beta _9}ROA + {\beta _{10}}YEA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 (3) |
模型(3)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引进了外部治理环境(INS)及其与高管薪酬的交互项SALARY×INS。其中,INS分别用政府干预GOV与法治水平LAW来替代。
(三) 变量说明1. 高管薪酬
由于学者们对于高管薪酬研究视角的不同,对其代理变量的选择也存在差异性。本文将报告期内高管前三名薪酬进行加总,取其总和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代理变量(李平和王玉乾,2015);将报告期内监事、董事、高管前三名薪酬进行加总,取其总和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替代变量(罗进辉,2014)进行稳健性检验。
2. 环境绩效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环境绩效研究角度的差异性,因此有关环境绩效的定义尚未统一。鉴于本文研究的是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因此采用的是Klassen和McLaughlin(1996)基于经济与环境绩效关系角度对环境绩效的定义,其认为环境绩效是企业在环境方面获得的奖励或惩罚。
虽然环境绩效这一变量在其相关研究中作用突出,但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环境绩效的统一规范评价标准(Poser等,2012)。国外学者所采用的环境绩效数据,主要是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14031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发布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生态效益指标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而国内学者由于环境绩效评分指数以及公司污染物排放数据库的缺乏,主要通过构建公司是否获得环境荣誉称号、是否因环境问题受到处罚与处罚类型、获得环境奖励级别、环保总局五色评分法等单指标或多指标环境评价体系赋值打分测量环境绩效。
对于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学者们利用较多的是有毒物质排放(TRI)数据。由于国内数据库的缺乏,本文选择WBSCD提出的生态效益指标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生态效益指标的表达式为:生态效益=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环境影响。鉴于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环境影响这两个变量不能直接获取,为保证测量的科学性,本文借鉴李平和王玉乾(2015)的做法,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用企业总营业收入(TOR)来表示,环境影响用排污费(ESC)来表示。
综上,环境绩效的计算公式为:CEP=ln(TOR)/ln(ESC)。
3. 外部治理环境
外部治理环境,反映的是企业治理的外部环境状况。本文用政府干预指数与法治水平指数构建了外部治理环境变量,用《报告》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指数分别代表政府干预指数(GOV)与法治水平指数(LAW)。《报告》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为反向指标,其越大,表明指代的政府干预水平越低;《报告》中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指数为正向指标,其越大,表明指代的法治水平程度越高。由于《报告》的数据只更新到2009年,根据李延喜等(2015)的建议,考虑到外部治理环境状况的相对稳定性,用2009年的外部治理环境数据来代替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
4. 其他变量
此外,根据相关文献,本文还引入企业所属行业、环境认证、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上市地点、盈利能力、样本年份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全部变量定义的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被解释变量 | 环境绩效 | CEP | 企业总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与排污费的自然对数之比 |
| 解释变量 | 高管薪酬 | SALARY | 报告期内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 |
| 外部环境治理 | INS | 包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 | |
| 政府干预 | GOV |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反向指标 | |
| 法治水平 | LAW |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指数,正向指标 | |
| 控制变量 | 所属行业 | INDUSTRY | 重污染行业①赋值为1,否则为0 |
| 环境认证 | ISO | 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赋值为1,否则为0 | |
| 企业规模 | SIZE |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
| 企业性质 | NATURE | 国有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 | |
| 上市地点 | MARKET | 在上交所上市赋值为1,在深交所上市赋值为0 | |
| 盈利能力 | ROA | 净利润与总资产平均值之比 | |
| 年份控制变量 | YEAR | 以2009年为基准变量,设置三个年度虚拟变量:YEAR10,YEAR11,YEAR12 |
①根据环保部2010年《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重污染行业包括纺织、化工、电解铝、建材、钢铁、发酵、石化、造纸、冶金、制药、水泥、酿造、煤炭、火电、制革和采矿业。
五、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 描述性统计表2是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中可以看出,高管薪酬的最小值为10.404,最大值为16.964,标准差为0.695,说明高管薪酬水平整体上差距较大。环境绩效的最小值为1.176,最大值为3.747,均值为1.508,说明样本企业的环境绩效总体水平不高。政府干预的最大值为10.00,最小值仅为–12.95;法治水平的最大值为8.74,最小值仅为–8.75,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
| 变量 | 样本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SALARY | 585 | 13.874 | 0.695 | 10.404 | 16.964 |
| CEP | 585 | 1.508 | 0.183 | 1.176 | 3.747 |
| GOV | 585 | 5.675 | 3.305 | –12.950 | 10.000 |
| LAW | 585 | 6.164 | 2.054 | –8.750 | 8.740 |
| INDUSTRY | 585 | 0.614 | 0.487 | 0 | 1 |
| ISO | 585 | 0.099 | 0.299 | 0 | 1 |
| SIZE | 585 | 22.468 | 1.289 | 19.822 | 26.272 |
| NATURE | 585 | 0.740 | 0.439 | 0 | 1 |
| MARKET | 585 | 0.615 | 0.487 | 0 | 1 |
| ROA | 585 | 0.033 | 0.048 | –0.326 | 0.381 |
表3是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的相关系数大于0.600,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外部治理环境的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为了避免模型中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将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变量分别放入模型(3)和模型(4)中回归,进行检验。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
| 1 CEP | 1 | |||||||||
| 2 SALARY | –0.131*** | 1 | ||||||||
| 3 GOV | –0.057 | 0.139*** | 1 | |||||||
| 4 LAW | –0.057 | 0.129*** | 0.870*** | 1 | ||||||
| 5 INDUSTRY | –0.189*** | 0.151*** | 0.044 | 0.071* | 1 | |||||
| 6 ISO | –0.067 | 0.001 | 0.140*** | 0.082** | 0.075** | 1 | ||||
| 7 SIZE | –0.213** | 0.452*** | –0.038 | 0.061 | 0.277*** | –0.107*** | 1 | |||
| 8 NATURE | –0.055 | 0.040 | –0.146*** | –0.088** | –0.054 | –0.077** | 0.260*** | 1 | ||
| 9 MARKET | –0.036 | 0.097** | –0.005 | 0.041 | 0.145*** | –0.079** | 0.087** | 0.084** | 1 | |
| 10 ROA | 0.021 | 0.178*** | –0.026 | –0.004 | 0.028 | –0.021 | –0.070** | –0.037 | 0.044 | 1 |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 ||||||||||
1. 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
表4是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中的高管薪酬回归系数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模型(2)中的高管薪酬回归系数值为0.629,高管薪酬二次方的回归系数值为–0.023,且都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此外,模型(2)调整后的R2大于模型(1),表明模型(2)的拟合度优于模型(1),假设1得到验证。
| 变量名称 | 模型(1) | 模型(2) |
| SALARY | –0.007(–0.56) | 0.629***(2.77) |
| SALARY2 | –0.023***(–2.81) | |
| GOV | –0.005(–1.03) | –0.006(–1.17) |
| LAW | 0.004(0.54) | 0.005(0.64) |
| INDUSTRY | –0.051***(–3.13) | –0.052***(–3.25) |
| ISO | –0.042*(–1.66) | –0.041(–1.62) |
| SIZE | –0.023***(–3.25) | –0.023***(–3.20) |
| NATURE | –0.013(–0.74) | –0.024(–1.32) |
| MARKET | –0.002(–0.12) | 0.002(0.12) |
| ROA | 0.058(0.35) | 0.032(0.19) |
| Constant | 2.189***(12.92) | –2.213(–1.40) |
| YEAR | Control | Control |
| Adj R2 | 0.255 | 0.266 |
| N | 585 | 585 |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 ||
2. 高管薪酬分组合理性检验
本文以高管薪酬水平的均值为界限进行分组,分成低高管薪酬组与高高管薪酬组。分组后低高管薪酬组有171个观察值,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剩余观察值中选取了相匹配的171个观测值作为高高管薪酬组,并采用模型(1)来对高管薪酬分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
由表5可知,低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0.055,在0.10水平上显著;高高管薪酬组中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0.104,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高管薪酬处于低水平时,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薪酬水平较低的高管会通过增加环境绩效来提升价值以期获得更高报酬;当高管薪酬处于高水平时,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薪酬水平较高的高管会通过降低环境绩效来规避风险以维护既得利益,这与假设1提出的结论一致。
| 变量名称 | 低高管薪酬组 | 高高管薪酬组 |
| SALARY | 0.055*(1.72) | –0.104**(–2.15) |
| GOV | –0.006(–0.82) | –0.010(–0.92) |
| LAW | 0.001(0.05) | 0.016(0.88) |
| INDUSTRY | –0.095***(–2.97) | –0.093*(–1.94) |
| ISO | 0.013(–0.27) | –0.106*(–1.66) |
| SIZE | –0.047***(–3.69) | 0.008(0.37) |
| NATURE | –0.012(–0.41) | –0.032(–0.77) |
| MARKET | 0.014(0.53) | –0.023(–0.61) |
| ROA | 0.163(0.68) | 0.011(0.02) |
| Constant | 1.864***(4.34) | 2.873***(3.95) |
| YEAR | Control | Control |
| Adj R2 | 0.318 | 0.224 |
| N | 171 | 171 |
3. 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表6是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通过表6可知,第2、3列是政府干预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低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0.172,且在0.01水平上显著;高管薪酬与政府干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值为–0.024,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此两项的回归系数值之和为正。而政府干预作为一个反向指标,由此可见,当高管薪酬较低时,政府干预显著弱化了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2a成立。高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0.175,高管薪酬与政府干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值为0.014,且均在0.10水平上显著,此两项的回归系数值之和为负。而政府干预作为一个反向指标,由此可见,当高管薪酬较高时,政府干预显著强化了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假设2b成立。
通过表6可知,第4、5列是法治水平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低高管薪酬组的高管薪酬回归系数值为0.169,高管薪酬与法治水平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值为–0.019,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研究假设3a不成立。高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0.234,且在0.05水平上显著;高管薪酬与政府干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值为0.021,且在0.10水平上显著,此两项回归系数值之和为负。由此说明,当高管薪酬较高时,法治水平显著弱化了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假设3b成立。
| 变量名称 | 政府干预 | 法治水平 | ||
| 低高管薪酬组 | 高高管薪酬组 | 低高管薪酬组 | 高高管薪酬组 | |
| SALARY | 0.172***(2.93) | –0.175*(–1.96) | 0.169(1.53) | –0.234**(–2.45) |
| SALARY×GOV | –0.024**(–2.36) | 0.014*(1.71) | ||
| SALARY×LAW | –0.019(–1.10) | 0.021*(1.84) | ||
| GOV | 0.306**(2.31) | –0.189*(–1.65) | ||
| LAW | 0.244(1.07) | –0.289*(–1.83) | ||
| INDUSTRY | –0.093***(–2.96) | –0.096**(–2.03) | –0.091***(–2.85) | –0.095*(–1.95) |
| ISO | –0.008(–0.18) | –0.105*(–1.66) | 0.003(0.06) | –0.010*(–1.73) |
| SIZE | –0.044***(–3.47) | 0.012(0.58) | –0.046***(–3.56) | 0.013(0.60) |
| NATURE | –0.019(–0.67) | –0.027(–0.67) | –0.013(–0.46) | –0.025(–0.61) |
| MARKET | 0.008(0.31) | –0.019(–0.50) | 0.011(0.40) | –0.023(–0.58) |
| ROA | 0.140(0.59) | –0.051(–0.10) | 0.177(0.74) | –0.034(–0.07) |
| Constant | 0.268(0.34) | 3.811***(3.07) | 0.359(0.24) | 4.579**(2.07) |
| YEAR | Control | Control | Control | Control |
| Adj R2 | 0.348 | 0.225 | 0.221 | 0.223 |
| Obs. | 171 | 171 | 171 | 171 |
为了增强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如前所述,以董事、监事、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测量指标,重复以上实证研究过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模型(1)中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模型(2)中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正,高管薪酬二次方的回归系数值为负,且均在0.01水平上显著,假设1成立。在政府干预影响的稳健性检验中,低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正,在0.01水平上显著,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值为负,在0.05水平上显著,且此两项的回归系数值之和为正,假设2a成立;高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负,在0.05水平上显著,高管薪酬与政府干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值为正,在0.10水平上显著,且此两项回归系数值之和为负,假设2b成立。在法治水平影响的稳健性检验中,低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和环境绩效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值并不显著,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假设3a不相符,但与实证中得到的“低高管薪酬时,法治水平不影响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一致;高高管薪酬组高管薪酬的回归系数值为负,高管薪酬与法治水平交乘项回归系数值为正,均在0.10水平上显著,且此两项的回归系数值之和为负,假设3b成立。综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前文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 变量名称 | 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 | 政府干预的影响 | 法治水平的影响 | |||
| 模型1 | 模型2 | 低高管薪酬组 | 高高管薪酬组 | 低高管薪酬组 | 高高管薪酬组 | |
| SALARY | –0.013(–1.01) | 0.739***(2.75) | 0.181***(2.92) | –0.188**(–2.35) | 0.161(1.53) | –0.237*(–1.68) |
| SALARY2 | –0.027***(–2.80) | |||||
| SALARY×GOV | –0.020**(–2.13) | 0.015*(1.67) | ||||
| SALARY×LAW | –0.016(–0.97) | 0.021*(1.69) | ||||
| GOV | –0.004(–0.94) | –0.005(–1.07) | 0.255**(2.08) | –0.209(–1.25) | ||
| LAW | 0.004(0.50) | 0.004(0.53) | 0.196(0.93) | –0.288(–0.97) | ||
| INDUSTRY | –0.051***(–3.16) | –0.052***(–3.23) | –0.084***(–2.65) | –0.101**(–2.06) | –0.085***(–2.65) | –0.094*(–1.94) |
| ISO | –0.043*(–1.67) | –0.040(–1.59) | –0.001(–0.00) | –0.107*(–1.69) | –0.010(–0.22) | –0.112*(–1.78) |
| SIZE | –0.022***(–3.08) | –0.022***(–3.15) | –0.046***(–3.73) | 0.015(0.70) | –0.046***(–3.69) | 0.015(0.72) |
| NATURE | –0.015(–0.83) | –0.025(–1.36) | –0.016(–0.57) | –0.038(–0.91) | –0.011(–0.40) | –0.036(–0.87) |
| MARKET | –0.002(–0.10) | 0.001(–0.00) | 0.009(0.37) | –0.020(–0.52) | 0.011(0.42) | –0.025(–0.66) |
| ROA | 0.074(0.45) | 0.039(0.24) | 0.131(0.56) | –0.115(–0.52) | 0.154(0.66) | –0.106(–0.22) |
| Constant | 2.239***(12.92) | –3.013(–1.60) | 0.195(0.23) | 3.595***(3.52) | 0.476(0.34) | 4.605**(2.37) |
| YEAR | Control | Control | Control | Control | Control | Control |
| Adj R2 | 0.256 | 0.267 | 0.350 | 0.238 | 0.331 | 0.234 |
| Obs. | 585 | 585 | 171 | 171 | 171 | 171 |
第二,借鉴沈洪涛等(2014)的做法,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的五色评分法对环境绩效这一变量进行赋值。鉴于国家环保总局将企业环境表现分为黑色、红色、黄色、蓝色、绿色五类,每类分别对应1、2、3、4、5分,将环境绩效相应替换为根据五色获得的离散型数据,重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根据比较可知,表8的回归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 变量名称 | 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 | 政府干预的影响 | 法治水平的影响 | |||
| 模型1 | 模型2 | 低高管薪酬组 | 高高管薪酬组 | 低高管薪酬组 | 高高管薪酬组 | |
| SALARY | –0.031(–0.56) | 2.151**(2.13) | 0.682**(2.29) | –0.698**(–2.23) | 0.856(1.53) | –0.487*(–1.87) |
| SALARY2 | –0.079**(–2.17) | |||||
| SALARY×GOV | –0.140***(–2.74) | 0.057*(1.66) | ||||
| SALARY×LAW | –0.144(–1.63) | 0.018*(1.68) | ||||
| GOV | 0.006(0.29) | 0.005(0.23) | 1.815***(2.71) | –0.814(–1.20) | ||
| LAW | –0.038(–1.16) | –0.036(–1.11) | 1.853(1.60) | –0.299(–0.25) | ||
| INDUSTRY | –0.318***(–3.71) | –0.286***(–3.30) | –0.501***(–3.16) | –0.339*(–1.97) | –0.495***(–3.08) | –0.292*(–1.72) |
| ISO | –0.292***(–2.63) | –0.292***(–2.64) | –0.251(–1.06) | –0.564**(–2.54) | –0.019(–0.72) | –0.546**(–2.47) |
| SIZE | –0.092***(–3.01) | –0.091***(–3.00) | –0.052(–0.82) | 0.018(0.24) | –0.062(–0.96) | 0.016(0.22) |
| NATURE | –0.002(–0.02) | –0.037(–0.46) | 0.010(0.07) | –0.219(–1.52) | 0.034(0.24) | –0.221(–1.55) |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从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两个层面研究了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与Bebchuk和Grinstein(2005)提出的过高的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一致;(2)政府干预弱化了低高管薪酬水平时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高高管薪酬水平时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3)法治水平对低高管薪酬水平的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与H3a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国内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惩罚力度相对较弱,而对薪酬水平较低高管的环境保护行为激励不足所致。高高管薪酬水平的法治水平弱化了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上述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与政府的环保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高管薪酬水平反映的是高管过去的经营业绩和管理品行,会影响高管对于当前环境绩效的行为决策。因此,作为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因素之一,企业在制定高管薪酬考核标准时,要考虑到环境绩效指标,将环境绩效水平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其次,从外部治理环境视角来看,政府应该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要提高法治水平,加大环境法规方面的执行力度,对环境绩效表现较差与较好的企业分别进行惩罚与奖励,营造关注和保护环境的企业氛围。
本文并未局限单一的线性关系研究,在理论与数据等方面丰富了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相关关系的文献。当然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1)关于外部治理环境的测量。本文选取的外部治理环境数据是从相对权威的《报告》中获得,但由于此数据更新较慢,因此缺乏最新数据,希望以后可以获得及时的外部治理环境数据来进行研究;(2)关于影响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分析。实际上,影响这两者关系的外部治理环境因素错综复杂,而本文仅从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两个主要层面进行分析,而忽视了金融发展水平、媒体舆论报道等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以上这些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 [1] | 李延喜, 陈克兢. 终极控制人、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14(9). |
| [2] | 盛明泉, 车鑫.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5). |
| [3] | 吕峻. 公司环境披露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2(12). |
| [4] | 沈洪涛, 黄珍, 郭肪汝. 告白还是辩白——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2). |
| [5] | 吴德军, 黄丹丹. 高管特征与公司环境绩效[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5). |
| [6] | 李平, 黄嘉慧, 王玉乾. 公司治理影响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5(2). |
| [7] | 夏立军, 方轶强.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 |
| [8] | 白俊, 连立帅. 国企过度投资溯因: 政府干预抑或管理层自利?[J].会计研究,2014(2). |
| [9] | 沈永建, 倪婷婷. 政府干预、政策性负担与高管薪酬激励——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6). |
| [10] | 张功富. 政府干预、环境污染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9). |
| [11] | 王耀东. 中国的环境污染与政府干预[J].财经问题研究,2016(2). |
| [12] |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 [13] | 李平, 王玉乾.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J].软科学,2015(9). |
| [14] | 罗进辉. 独立董事的明星效应: 基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考察[J].南开管理评论,2014(3). |
| [15] | 李延喜, 曾伟强, 马壮, 陈克兢. 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J].南开管理评论,2015(1). |
| [16] | Bebchuk L, Grinstein Y. The growth of executive pay[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5,21(2):283–303. |
| [17] | Berrone P, Gomez-Mejia L 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 integrated agency-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9,52(1):103–126. |
| [18] | Boubakri N, Cosset J C, Saffar W.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8,14(5):654–673. |
| [19] | Collett P, Miles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Exploring the link[J].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2013,9(1):76–90. |
| [20] | Cong Y, Freedman 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disclosures[J].Advances in Accounting,2011,27(2):223–232. |
| [21] | Conyon M J, He L 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4):1158–1175. |
| [22] | Dawkins C, Fraas J W. Coming clea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visibility on corporate climate change disclosur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100(2):303–322. |
| [23] | Fama E F.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2):288–307. |
| [24] | Qi G, Zeng S, Tam C M. Stakeholders’ influences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3,20(1):1–14. |
| [25] | Hoffman A J. Competi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 guide to the changing business landscape[M]. Znd ed.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0: 50–51. |
| [26] | Iatridis G 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quality: Evidence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value relevance[J].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13,14:55–75. |
| [27] |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
| [28] | Jensen M C, Murphy K J. 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2):225–264. |
| [29] | Klassen R D, McLaughlin C P.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n firm performance[J].Management Science,1996,42(8):1199–1214. |
| [30] | La Porta R, Lopez-de Silanes F, Shleifer A. Law and financ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6):1113–1155. |
| [31] | Melo T, Garrido-Morgado A. Corporate reputation: A combin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y[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2,19(1):11–31. |
| [32] | Menguc B, Auh S, Ozanne L.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 a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its influence on a firm’s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4(2):279–298. |
| [33] | Meng X H, Zeng S X, Shi J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4,145:357–367. |
| [34] |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Z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23. |
| [35] | 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Norton, 1981: 30–32. |
| [36] | Poser C, Guenther E, Orlitzky M. Shades of green: Using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different aspec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Control,2012,22(4):413–450. |
| [37] | Zou H L, Zeng S X, Lin H. Top executives’ compensation,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Management Decision,2015a,53(9):2036–2059. |
| [38] | Zou H L, Zeng S X, Xie L N. Are top executives rewarded f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J].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5b,21(6):1542–1565. |
 2017, Vol. 19
2017, Vol.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