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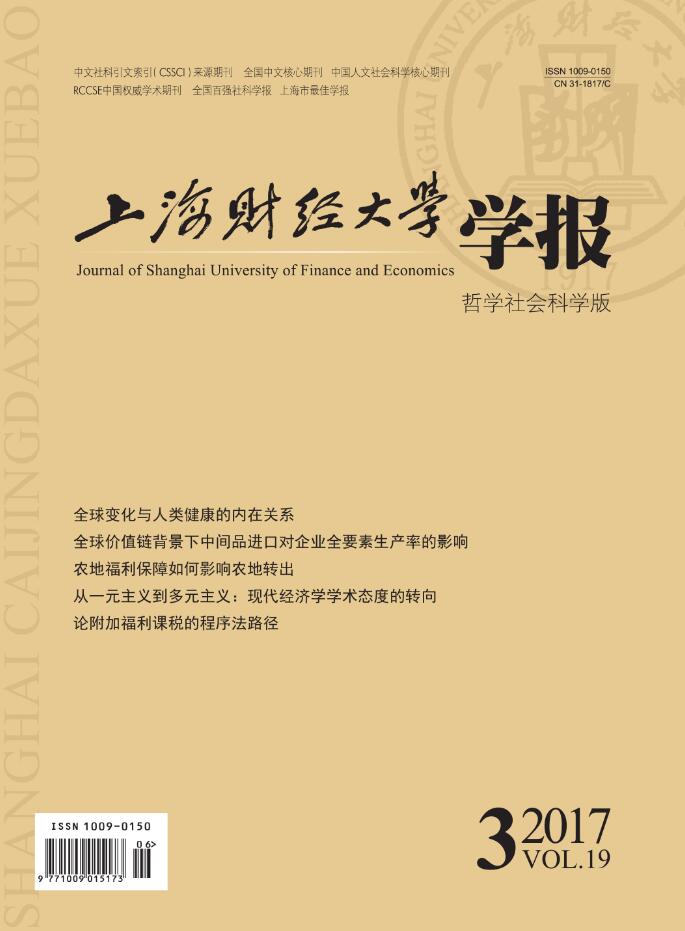 |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19卷第3期 |
- 顾雪兰, 刘诚洁
- Gu Xuelan, Liu Chengjie
- 健康投资与健康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
- The Dual Effect of Health Investment and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 19(3): 22-30.
-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7, 19(3): 22-30.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7-03-11

2017第19卷第3期
2.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不断攀升等问题的日益凸显,我国健康投资水平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家庭层面来看,1990–2015年间城市人口健康保健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从2%上升到6.5%,农村人口中的这一比例则从3.3%上升到9.2%,健康支出在家庭支出中的占比显著提升;从政策层面来看,2000年政府健康支出占总健康支出的比重为15.5%,这一比例到2015年已上升为30.4%,上升幅度达96%左右,政府对公共健康事业的支持力度大幅增加。①然而,随着不断攀升的健康投资,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却并未有显著提高,反而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
如何解释这一经济现象,理论界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关于健康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讨论,美国经济学家Fisher早在1909年就有分析,他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指出,健康是国家的财富,增加健康方面的投入能减少疾病损失,并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然而,健康投资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具体机制,他并没有作出较为深入的解释。1961年,Schultz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是对教育进行投资形成的资本,而且包含教育、健康和移民等多方面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这是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创新性解析;②而Mushkin在1962年则正式提出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的概念由此形成,并认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孪生产物。①此后,诸多国内外学者从多种途径肯定了健康人力资本对国民产出水平的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是认为健康状况会影响劳动者体力和精神状态,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二是认为健康水平会影响劳动供给,从而影响家庭收入和经济产出;三是认为健康条件会影响死亡率和出生率,从而促使净人口再生产率发生变化;四是认为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国民受教育情况,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五是认为健康影响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决策,继而影响储蓄及物质资本投资。因此全面解析了健康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
①数据来源:《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http://www.cpc.unc.edu/projects/china/。
②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1):1-17.
①Mushkin S J. Health as an Invest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70(5):129-157.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国内学者也陆续展开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一是多数学者都证明了通过健康投资会促使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提高劳动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健康投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蒋萍等,2008)。二是也有学者认为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促进作用,通过健康投资,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伴随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也会进一步促进健康投资的增加,从而健康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随之提高,即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影响,互为因果(王学文,2014);三是健康投资也有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用于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势必会对当期的物质资本投资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占,妨碍经济快速增长(杨建芳等,2006;王弟海等,2008)。
与此同时,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相对于城市的不完善,部分学者特别关注了健康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影响,王翌秋和刘蕾(2016)认为由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导致农民承担了巨额的健康支出,并因疾病对农户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经济发展。刘国恩等(2004)通过在健康人力资本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中对比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健康收益,得出如下结论: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人口健康的收益更大,而且女性的健康收益比男性大。不仅如此,饶勋乾和成艾华(2007)认为,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较大,各地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也各异,表现为东、中、西部逐步递减。在此基础之上,付波航等(2013)研究发现,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
可见,目前理论界关于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综观现有研究,仍能发现一定的发展空间。
一是现有研究大多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出发来考察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从健康经济增长角度来分析问题,并界定健康投资与健康经济增长的内在涵义及其作用机理。
二是在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上,大多认为健康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我国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之后,国内学者众多的实证研究都肯定了在中国近30多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健康人力资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对于短期中健康对经济可能存在的反向效应研究却还很少。现有学者在研究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多是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或是协整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此理论基础上的实证结果也都肯定了公共健康支出在我国经济“奇迹”中的重要作用。虽然也有研究涉及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但也仅在于实证分析并没有做出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对和对其作短期与长期的区分。
对此,本文将从人类健康的根本需求出发,从健康经济增长的新理论视角切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之下,剖析健康投资与健康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内涵,进而分别从短期和长期去阐明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的正反向作用关系和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的现实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相关结论,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
二、健康投资与健康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传统经济增长,也即当前全球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单个资本所有者在预算约束下进行的利益最大化选择的产物。这一预算约束在最初主要表现为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成本,其后随着国家加强对污染物排放的管制并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治理污染的成本也部分纳入了预算约束的范围内。然而,截至目前,人类健康这一要素却始终未能成为企业做出行为选择时的重要约束条件,这就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并未考虑到人类健康的保障和提高,反而常常以牺牲部分人的健康作为发展的代价。
当前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并不符合人类发展的长期取向。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主要包括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而这五个方面中均隐含着对健康的需求。从较高层次而言,决定自我实现、尊重、爱和归属感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为,社会环境是否健康、和谐;从较低层次而言,安全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健康保障,当人类对健康保障的安全感降低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提高健康保障的行为激励,而生理需求则更是与健康密切相关,在人类健康水平持续恶化的条件下,生理需求必将受到威胁从而促使受到威胁的群体采取行动。可以说,健康是人类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和底线,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关于健康经济增长与健康投资的内涵与作用机制分析
所谓健康经济增长是将人类健康作为重要约束条件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传统经济增长相对应,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健康经济增长应以人类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而不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第二,健康经济增长应以健康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为主要动力,而不是物质资本;第三,健康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提高。因此,健康的经济增长能够满足人类对健康和物质财富的双重需求。
然而,从传统经济增长到健康经济增长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逐步提高健康投资的额度、改善健康投资结构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途径。
所谓健康投资,“简而言之,就是为劳动力的健康而进行的投资,因而这一投资具有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所以,也可以称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①。狭义的健康投资主要指为预防和治疗疾病、恢复人体健康而支出的费用,即医疗卫生费用。广义的健康投资则是指整个社会为预防与治疗疾病,维持和增加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活动能力、劳动生产能力,恢复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而投入的全部经济资源。”②所以,健康投资是修复和改善人类健康状态的投资,也是形成健康劳动力或健康人力资本的基本途径。健康投资也有结构性效应,如果健康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到疾病的治疗上,则仅能维持现有人类健康程度,很难实现人类健康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相反,如果健康投资能够合理地分配到保健、预防、基本医疗服务、疾病治疗等各个环节,则有利于提升健康投资的效果,加快由传统经济增长到健康经济增长的转变。
①本文将健康劳动力与健康人力资本通用,而不做严格区分
②赵国宝:《健康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4。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综合产出水平是由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四个因素的投入所决定的。由于健康投资是健康劳动力或健康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健康投资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对经济产出产生影响:
(1)通过健康投资形成健康劳动力,而这些健康劳动力创造更多利润,进而推动经济健康增长;
(2)健康投资形成更加复杂的健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创新性活动推动技术进步,间接推动经济健康增长;
(3)健康投资促使健康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增长;
(4)健康投资在形成健康劳动力或健康人力资本的同时,也会影响物质资本更加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发展,减少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遭受的环境污染,从而避免影响健康。
健康投资对于健康经济增长并不是单纯的促进作用,而是具有双重效应。一是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抑制效应,即当我们把健康作为约束条件引入经济增长之中,必然会增加健康资本投资的部分,从而挤占了物质资本,影响生产规模,经济无法保证持续有效的增长;二是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健康的劳动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就整个社会来看,健康投资也会降低各类疾病的发病率,改善劳动者及其家庭子女的生活状况,同时降低死亡率,延长人均寿命,保证劳动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达这一问题,我们运用数理模型分别就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的短期抑制效应和长期促进效应进行分析。
(二)关于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抑制效应分析
首先,在短期内,健康投资对于健康经济增长不会迅速的发生作用,而只是作为一种沉淀成本形式存在。这是因为健康投资不同于一般的投资,它是对劳动力的健康恢复、修复、维持和提升的一种投资,健康恢复投资是将已经丧失的健康重新复原,健康修复投资是将已经损失或损坏的健康修补好,健康维持投资是保持现有健康状态,健康提升投资是提高现有健康水平。可见,无论是哪一种健康投资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就是说,在短期内健康投资尚不能形成有效的健康人力资本,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短期下降。与此同时,如果将投资于健康人力资本的部分用于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即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则当期的活劳动就会增加,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对于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短期无法显现其应有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为此,我们称短期健康投资资本为短期沉淀成本。
其次,在短期内,由于资本投资总量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当增加健康人力资本后,就会对物质资本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出,从而导致企业的物质生产规模减少。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企业每一期都必须将固定比例的剩余价值用于积累和投资,即生产的扩大同时需要相应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与其匹配,生产才得以进行,然而,在积累率和剩余价值率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当期进行了健康投资,即增加了可变资本,这样势必会挤占不变资本,影响不变资本c的增加。相应的在资本有机构成c/v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数量也会减少,从而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因此,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现实作用也不确定,若正向作用大于反向作用,表明健康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发生了长期的促进作用;反之,则是短期的抑制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数量关系的变化,我们具体假设如下:
(1)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cp、一般人力资本vp和健康人力资本vh;
(2)假设在短期内,在总投资量一定的条件下,增加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减少物质资本投资,即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量就是物质资本投资的减量,表达为:
| ${v_h} \uparrow \Rightarrow {c_p} \downarrow $ | (1) |
(3)假设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在短期内具有沉淀效应,不会对经济增长立即发生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将没有考虑健康投资的总资本投资C结构记为:
| $C = {c_p} + {v_p}$ | (2) |
将考虑健康资本投资的总资本Ch结构记为:
| ${C_h} = {c_p} + {v_p} + {v_h}$ | (3) |
如果健康人力资本对于健康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作用为零,即vh=0,故C>Ch,即在短期内,一般经济增长速度会快于健康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假设C为上期资本投资总量(不包含健康投资),Ch为当期资本投资总量(包含健康投资),显然,健康投资增长率减少,
结合上述分析,从短期效应来看,健康投资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一方面,体现在用于健康投资的可变资本成为短期沉淀成本,并不创造剩余价值,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健康投资的可变资本增加对扩大再生产中不变资本的持续增加造成挤出,从而导致企业生产规模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健康投资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将弱于负向抑制作用,致使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此时,如果不能持续地提高健康投资,而是使健康投资成为阶段性行为,则经济增长会重新回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反之,如若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保证健康投资的持续性、累积性增加,使得健康投资从修复性投资跨越到提升性投资,则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将进入长期促进状态。
(三)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分析
首先,在长期内,由于健康人力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健康恢复、修复、维护和提升的效应显现,并由沉淀成本转变为可变资本,从而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还会促进经济增长,即作为健康投资的可变资本被激活,形成有效的健康人力资本,开始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其次,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还会形成倍加的劳动效应,即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个体健康劳动力不仅具有健康的体魄可以承担更高的劳动强度,而且还会由于健康劳动力在身体健康的同时,心理和智力也都健康发展。提升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样可以激发出他们的潜在劳动能力和创新性劳动能力,使其劳动由简单劳动转化为复杂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以促进健康经济增长。
再次,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也将改善整个社会劳动者身体状况,提升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延长人均寿命,并保证家庭和未来劳动力的健康,从而持续的提供健康的劳动力供给,以满足健康经济增长对于健康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保持健康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此外,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作用的凸显,也要求物质资本在材料质量、生产过程中也更加健康环保,以至于在质量上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匹配,符合健康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从而保持健康经济增长的完全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述数量关系的变化,我们具体假设如下:
在长期内,当健康人力资本被激活,则vh>0,这样,健康投资率将提高或不变,
因此,从长期效应来看,健康投资与健康经济增长会呈现协同提高。健康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形成具有可持续性且效率不断提升的劳动力供给,还会促进社会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升,使得健康劳动力具有倍加的效应,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增长;与此同时,健康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促进健康投资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的健康程度。此时就形成了“健康投资—健康经济增长”之间循环的良性互动关系,其结果是人类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总之,人类对健康的基本需要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是健康经济增长,而健康投资是促进传统经济增长向健康经济增长转变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转变过程,短期内经济可能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增速放缓,但这是长期内形成“健康投资—健康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
三、实证分析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将利用1980–2014年的全国统计数据来对中国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厘清当前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增长转向健康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处的阶段,继而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健康投资不断提高与健康水平不断下降的悖论进行解析。
(一)模型设定及检验假设
根据前文所述,从长期看健康投资能形成健康人力资本,促使经济增长,但在短期内会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由此,我们建构回归模型如下:
| ${g_t} = {\beta _0} + {\beta _1}{h_t} + {\beta _2}{p_t} + {\beta _3}{r_t} + {u_t}$ | (4) |
| ${p_t} = {\beta _0} + {\beta _1}{r_t} + {u_t}$ | (5) |
其中,gt表示t年的人均GDP增长率,h表示人均健康投资,r表示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p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如下两个有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健康投资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假设2:健康投资会对物质资本投资产生挤出影响,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选择
为探讨健康投资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我们通过查阅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收集并处理1980–2014年间的各类统计调查数据,主要包括下述三个方面的指标。
(1)经济增长指标:众多文献表明,人均GDP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最优指标,因此本文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年鉴获得人均GDP数据,而后计算得到人均GDP增长率(g)的数据来作为经济增长指标。
(2)健康投资指标:狭义的健康投资即指医疗卫生费用,因而,本文健康投资主要采用每年卫生总费用数据,来计算得到人均健康投资(h)数据。每年卫生总费用数据由查阅卫生统计年鉴得到。并且计算得到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r)数据。
(3)物质资本投资指标:本文以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物质资本投资指标,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年鉴得到,并计算出人均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均物质资本投资增长率(p)数据。
(三)实证分析
首先,在对上述4个变量进行简单处理之后,可以得到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表1中的数据显示出,人均GDP增长率(g)与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r)、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p)均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p)与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r)则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该结果表明健康投资的增加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物质资本的增加产生抑制作用。
其次,在假设物质资本增长率p=0的情况下,我们在SPSS软件上对人均GDP增长率(g)、人均健康投资(h)和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r)做线性回归,通过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来研究健康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回归方程如下:
模型1
| ${g_t} = {\beta _0} + {\beta _1}{h_t} + {u_t}$ | (6) |
模型2
| ${g_t} = {\beta _0} + {\beta _1}{h_t} + {\beta _3}{r_t} + {u_t}$ | (7) |
表2中列示了上述回归的结果,其中,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r)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物质资本不增长,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对人均GDP的增长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 模型1 | 模型2 | |
| constant | 0.156*(10.361) | 0.014(0.417) |
| h | –0.179(–1.046) | –0.088(–0.64) |
| r | 0.622*(4.535) | |
| R-square | 0.032 | 0.374 |
| 注:n=35,括号中数值为t值,*p<10。 | ||
最后,为讨论健康投资对于物质资本的影响,我们把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引入计量模型,重新建立计量模型:
模型3
| ${g_t} = {\beta _0} + {\beta _1}{p_t} + {u_t}$ | (8) |
模型4
| ${g_t} = {\beta _0} + {\beta _1}{r_t} + {\beta _2}{p_t} + {u_t}$ | (9) |
表3中列示了上述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人均GDP增长率对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和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健康投资增长率以及物质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影响。而在之前的相关系数表中,健康投资增长率与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负的。将两个结论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健康投资会负向影响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从而减少物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模型3 | 模型4 | |
| constant | 0.145*(11.570) | 0.004(0.132) |
| p | 0.058(0.334) | 0.079(0.583) |
| r | 0.638*(4.691) | |
| R-square | 0.003 | 0.410 |
| 注:n=35,括号中数值为t值,*p<10。 | ||
(四)实证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一是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均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增加健康投资和提高物质投资水平都能够促进健康经济增长,而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与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则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健康投资的增加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物质资本的增加产生抑制作用;二是在物质资本不增长的前提下,人均健康投资增长率对人均GDP的增长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即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将前面两个结论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健康投资会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而且是通过对物质资本的挤出效应来抑制经济增长的速率。
四、政策建议通过以上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1)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人类健康的基本需求,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必然是健康的经济增长;(2)健康投资是实现健康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分;(3)要真正实现健康投资与健康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必然要经历一段健康投资抑制经济增长的过渡阶段;(4)中国当前仍处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之下,健康中国的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对健康和卫生事业的建设工作一直没有松懈,并且对其的投入一直在增加。2007年党的“十七大”会议首次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新要求”,并强调“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同年11月,国家18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年)》;2008年卫生部启动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并于2012年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观点;2016年8月19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战略,并且强调了大力发展健康产业的重要意义;①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的“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形成。
然而,尽管我国政府在卫生总费用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投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状况都在不断改善,但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前的健康投资依然存在总量较少、区域差异明显、城乡差异较大等问题,这显然不足以支撑我们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向健康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过渡。因此,为了保证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针对如何提高我国当前居民健康投资水平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经济增长向健康经济增长的转变。有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仍处于健康水平较低的阶段,从1990年到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36.32倍,而卫生总费用却提高了54.82倍,政府卫生支出占总费用的比重由25.06%增加到30.45%,社会卫生支出占总费用比重由39.22%提升到40.29%,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总费用比重由35.73%降低到29.27%,②与此同时,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所谓的“短期效应”,即健康投资严重不足,由此发现,我国正处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向健康经济方式转变阶段。因此,增加健康投资是实现健康经济增长方式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增加健康投资具体来说,可分为提高个人健康投资水平和扩大政府健康投资比例。
①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8月19日。
②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计算而得。
第二,提高个人健康投资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渐渐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的富有,逐步开始关注自身健康水平的维持和保护。然而当前人们对于健康的整体认知还处在较低水平,健康意识薄弱,认为对于健康的投资不属于资本投资;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健康投资在未来的效益,认为健康投资是一种经济负担,只有在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满足之后才会进行一些基础的健康投资。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健康意识的基本宣传和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健康投资的意识,同时积极倡导健康产业的发展,让人们意识到个人增加健康投资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通过提高自身的劳动水平来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更是一种为整个社会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有益行为,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益的分配的社会贡献。
第三,扩大政府健康投资比例。由于我国目前的健康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所以政府对于健康投资的态度和观念是提升我国健康医疗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一直以来,政府都只是把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看作保障社会公平的福利性支出,没有树立起健康是一种投资的观念。本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健康可以通过增加健康人力资本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在短期内,由于对物质资本积累的负向影响,健康投资的效益不会明显显现,甚至有所阻碍,但政府应当看到健康投资的长远影响,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它所能带来的未来效益将是巨大的。因此,政府应当不断扩大对改善公共健康状况的投资,其中尤其包括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投资支出,生存环境的优劣与居民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政府有义务为广大居民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还应当注重宣传和教育,政府的重视和投入会带动个人和集体,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样不仅有助于扩大政府的公信力,还能促使健康产业大步迈进。
| [1] | 付波航, 方齐云. 健康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地区差异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3(9). |
| [2] | 付波航, 方齐云, 宋德勇. 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11). |
| [3] | 蒋萍, 田成诗, 尚红云. 人口健康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5). |
| [4] | 刘国恩, William H. Dow, 傅正泓, 等. 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 经济学, 2004, (1). |
| [5] | 吕娜. 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1. |
| [6] | 饶勋乾, 成艾华. 健康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比较[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9). |
| [7] | 王弟海, 龚六堂, 李宏毅. 健康人力资本、健康投资和经济增长——以中国跨省数据为例[J].管理世界,2008(3). |
| [8] | 王煜, 张斓, 黄建始. 健康投资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1). |
| [9] | 王学文. 我国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14, (3). |
| [10] | 王翌秋, 刘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 (11). |
| [11] | 杨建芳, 龚六堂, 张庆华.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5). |
| [12] | 赵国宝. 健康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4. |
| [13] | Barro R J. Health,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R]. Washington DC: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1996. |
| [14] | Grossman M.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R]. NBER Working Paper, No. 7078, 1999. |
| [15] | Mushkin S J. Health as an Invest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70(5):129–157. |
| [16] |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17. |
2.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2017, Vol. 19
2017, Vol.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