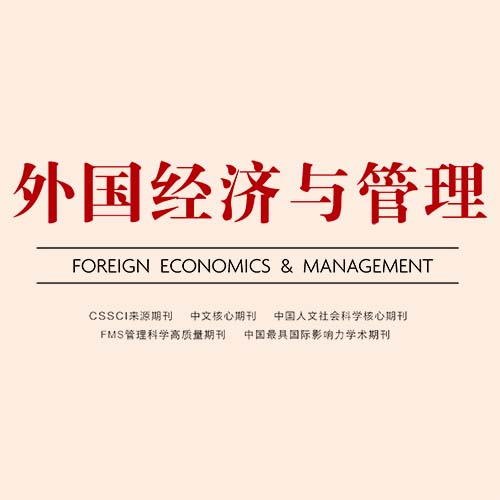
2025第47卷第5期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3.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710
2.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Guangzhou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510710, China
创业研究源自经济学(朱仁宏,2005;Foss等,2019)。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先后出现了多个理论流派以解释创业活动的复杂过程(周冬梅等,2020)。然而,正如福斯等学者(Foss和Klein,2012;Foss等,2019)的研究发现,目前一些主流的创业理论如机会观、资源观等否定了外部情境与内部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Swedberg,2006),因此无法将制度、文化等背景因素作为重要的变量纳入到研究框架之中。实际上,创业是一个“背景依存性的社会过程”(Jack和Anderson,2002)。新创企业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动态之中,理解创业现象就必须关注创业过程中包含的文化动态,即新创企业的自我身份构建以及组织合法性获取等文化问题(倪宁和李钊仪,2016)。不考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新创企业和创业者与作为外部环境的制度、文化等背景之间的互构,我们就无法对鲜活的、丰富的创业现象做出准确的认知(Patriotta和Siegel,2019)。文化创业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倪宁和李钊仪,2016;Gehman和Soublière,2017;Lounsbury等,2019;Lounsbury和Glynn,2019;王家宝等,2021)。该理论基于当代文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文化作为行动者的资源,作为一种在不同背景下构建行动策略的可能性的工具包(Swidler,1986),帮助创业者在组织有形的创业资源之前运用讲故事等方式来动员活动以获取合法性(王家宝等,2021)。文化创业理论的提出不仅为创业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因为只有它才有可能更好地解释“从无到有”的创业过程如何得以实现(倪宁和李钊仪,2016;Lounsbury等,2019)。
文化创业的概念最先由DiMaggio(1982)提出的,而对文化创业理论起到开创性作用的是Lounsbury和Glynn(2001)。在随后20多年里研究者们开展了大量的拓展性研究,使得文化创业的理论体系日益优化和完善。不过遗憾的是,一方面文化创业的文献虽然丰富,但是大多数呈现为零散化、碎片化的态势,对完整理论体系进行归纳和总结的研究和综述都比较匮乏
鉴于目前文化创业理论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上述问题,需要对文化创业理论体系进行梳理,明确其核心概念、厘清其理论边界,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方向,并探索其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有利于从文化层面推动中国的“双创”实践。因此,本研究选择2001年作为建立文献库的时间起点,以“文化创业”“创业+故事”“创业+叙事”“创业+话语”“创业+修辞”等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以“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story”“entrepreneurial+narrative”“entrepreneurial+discourse”“entrepreneurial+rhetoric”等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检索,从管理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7本期刊和创业领域重要的3本期刊
(一)文化创业的内涵
显然,文化创业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文化创业。Gehman和Soublière(2017)指出,文化创业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相互独立的演进阶段,分别是“文化创业1.0”阶段——该阶段的核心是创建文化(making culture)、“文化创业2.0”阶段——该阶段的核心是部署文化(deploying culture)和“文化创业3.0”阶段——该阶段的核心是文化创造(culture making),不同阶段其概念的内涵有较大的差异。
文化创业1.0起源于社会学,聚焦于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创建文化,特别是组织形式、治理结构和文化产品,涉及范围从博物馆、交响乐和歌剧到流行音乐公司、电影节和独立音乐制作人(Johnson,2007)。在这一阶段文化创业被定义为“进行新颖的组合,从而在文化领域产生新的东西并受到赞赏”(Swedberg,2006)。在这里文化被视为一个部门或一组产业,考察的重点是该部门或产业的创业活动。这一阶段“文化创业”的标签主要被贴在创意或文化领域(如艺术、建筑、音乐、时尚、电影等)的特定创新创业活动上,没有提出一个广泛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内涵,因此概念的界定只是揭开了文化创业理论创建的序幕,并没有涉及该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只能说是文化创业理论在文化产业部门的一种具体体现。
正是因为文化无处不在、具有普遍性,文化创业不能只关注艺术和创意领域的独特之处,还要考察不同背景之下创业过程的共性、解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和结果,包括高科技企业、大型跨国公司等的创新创业现象。Lounsbury和Glynn(2001)开创了文化创业的第二条道路,即文化创业2.0阶段。文化创业被定义为“在企业现有的资本存量与随后的资本获取与财富创造之间发挥重要作用而进行讲故事的过程”,这一阶段试图发展一种更广泛、动态和多层次的文化创业理论。文化创业强调的是,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如何对其初创公司展开形象管理,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沟通以获取其合法性的认同,最终实现资源获取和财富创造的目标(王家宝等,2021)。在文化创业的道路上,熟练的文化创业者是关键,故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是核心,企业内部现存的资源和资本存量是基础,企业对独特且合法的创业身份的构建是目标,资源和财富的获取是结果。而故事作为核心所在既能推动又能阻碍文化创业的成功,关键在于文化创业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对企业现存资源和资本存量的运用。一个完整的故事通常都包含相似的内容要素:人物、目标及事件(Fiol,1989),故事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知和了解世界,还有助于体会和激发相互情感(Escalas,2004)。文化创业2.0聚焦于部署文化,即文化创业需要通过将可用的点点滴滴的文化拼凑成一致且引人注目的身份,从而使新创企业合法化。
应该说,Lounsbury和Glynn(2001)提出的文化创业概念即文化创业2.0及其内涵标志着文化创业理论的诞生。该理论的逻辑框架和体系内容基本上是建立在此概念内涵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是前后相承,但文化创业1.0和文化创业2.0几乎没有交集,是并行发展的。文化创业1.0成为了在艺术和文化产业中变革的标签,而文化创业2.0在对新创企业感兴趣的管理和组织领域的学者中广为流行(Gehman和Soublière,2017)。
文化创业3.0则是在2.0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Giorgi等,2015)。这一波新的研究重点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创造还是部署文化,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文化创造”方面。学者们从框架、价值观、工具包、类别等多种文化概念中汲取灵感,认为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创业行为的媒介(部署)又是其结果(创造),文化创业表现出“文化创造”的特质。文化创业3.0被定义为“一个不断构想和重新构想未来愿望和过去事件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业故事也会不断地发展”(Garud等,2014)。文化创业3.0聚焦于文化创造,突破和发展了文化创业2.0,更强调构建的意义,强调文化创业是一个分散的、跨时期的过程,也是一个跨多个领域且多变的要素和意义创造价值的过程(Gehman和Soublière,2017)。
从以上文化创业内涵的演进可以看出,文化在创业活动中所具有的能动性越来越强(由创建文化到部署文化再到文化创造),运用文化工具开展创业活动涉及的范围也由独特趋于广泛(从最初的文化创业领域拓宽至各行各业),但是其核心机制——通过讲故事以构建身份获取合法性却贯穿于始终。
(二)文化创业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的比较
文化创业理论不仅拥有独特的核心概念,而且还具备独立的内容体系和思想观点。虽然有部分学者会将其与另外一些有着密切关系的既有理论尤其是印象管理理论进行对照,并提出是否能够称其为一种理论的质疑(于晓宇和陈依,2019),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还是支持和认同文化创业理论的合法性的。通过将两种理论进行细致的比较,有助于明确文化创业理论及其核心概念的适用条件。
印象管理起源于社会心理学,Baron和Markman(2000)首次将其引入创业领域,指的是“创业者为实现某些有价值的目的而对自我或企业形象进行主动控制的过程”(于晓宇和陈依,2019)。通俗地说,就是在为创业者或企业“立人设”(王家宝等,2021)。但是,印象管理理论在构建身份获取合法性的解释上是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在印象管理理论看来,创业者或新创企业构建什么样的身份完全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期待,构建身份的目的就是迎合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判断(Nagy等,2012)。由此所构建出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之上的,甚至有可能是虚假和编造的(Bolino等,2008)。再借助于信息不对称,不真实的身份被刻画为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为其所接受认同并赋予合法性资源。然而,这种因利益而虚构的“人设”由于缺乏事实基础而总有“真相败露导致人设崩塌”的一天(王家宝等,2021),因此建立在这基础上的身份形象是不能持久的,必须随着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变化而动态调整,否则最终有可能被识破而遭到厌恶和抛弃。这也是印象管理理论为什么强调身份的构建和塑造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原因(金婧,2018)。而基于文化创业理论的视角创业者或新创企业身份的构建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虽然故事的讲述可以采用隐喻、类比等多种修辞策略(倪宁和李钊仪,2016),但是构成故事主线的数据和信息一定是与事实相符的。因此,建立在这基础上的身份形象是与其原型非常贴近的,可以持久而稳定。毕竟,在文化创业理论看来,构建新身份的目的不仅是获取合法性资源,还要能够将自身与其他在位企业区分开来,彰显一定的独特性(Lounsbury和Glynn,2001,2019)。为此,新的身份形象不只是为了符合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还要针对他们的不同讲述更符合其认知的差异化故事(Fisher等,2017)。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让每一位利益相关者都可以通过身份形象较为客观完整地了解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而不是故意为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与此同时,文化创业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也存在着相互补充的部分。第一,文化创业理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对新创企业创始人或组织新身份的构建上,可以对印象管理理论基于创业背景下的身份构建或维持起到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第二,在身份构建的具体途径上,文化创业理论强调了讲故事的重要作用,这也为印象管理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选择。无论是声明还是辩解、道歉,归根结底都需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认同。而故事特有的传奇性、曲折性、冲突性、戏剧性、传播性和传承性,使其更容易抢占人心(汪涛等,2011)。因此,印象管理理论可以将故事运用于其构建和维持身份的主要途径之中。两种理论的区别和联系如下表1所示。
| 文化创业理论 | 印象管理理论 | |
| 前提假设 | 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 信息不对称 |
| 目标 | 构建新身份 | 构建新身份或维持旧身份 |
| 结果 | 获取合法性和资源、建立最优区分 | 获取合法性和资源 |
| 作用机制 | 对个体或组织身份进行有意识的构建 | 对个体或组织身份进行主动的控制 |
| 主要途径 | 讲故事 | 声明、辩解、道歉、叙事等 |
| 常用策略 | 修辞策略 | 获得性策略、防御性策略 |
| 应用场景 | 新创企业 | 新创企业、成熟企业、污名化企业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 ||
Lounsbury和Glynn(2001)开创了文化创业理论,提出了经典的理论框架并对其作用机制首次做出了完整的阐释。后续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补充完善,使得文化创业的理论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改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Garud等(2014)以及Lounsbury等(2019)。
(一)文化创业理论的经典作用机制
Lounsbury和Glynn(2001)最先提出了文化创业理论的理论框架,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完整的阐述。研究的初衷是解决新创企业由于其新颖性和独特性而缺乏一些事实性的证据(例如业绩记录等)来得到外部验证(合法性),进而获取所需资源的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了文化创业的概念,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反映文化创业的作用机制(见图1)。
该理论框架的重点就是如何根据现有的资本存量利用创业故事去合理建构企业身份,使投资者、竞争者和消费者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赋予新企业合法性,从而开拓获得新资本和市场机会的途径。其作用机制说明如下:首先,现有的资本存量是创业故事的基础。要想成功吸引投资者,创业故事不能仅是简单地提出身份声明,还要反映出企业的资本存量,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业故事可以通过由资源资本和制度资本这两种关键创业资本形成的重点内容帮助企业创造竞争优势。两者同时强调了企业的能力和背景,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其次,故事可以作为企业的合法身份说明。一般来说,创业故事的叙事主体是创始人或新创企业,叙事的最终目标是盈利或良好声誉等,目的地是叙事主体所在的公司或社会环境。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创业故事必须具有叙事保真度,并与潜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利益产生共鸣(王泽民等,2024)。创业故事必须在战略独特性需求与行业规范性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即当企业的制度环境具有合法性或企业的经营相对于行业现有专业知识或实践而言是一种颠覆时,则较多地强调独特性,否则,较多地强调规范性。最后,获取资本和创造财富。创业者通过创业故事使新创企业合法化,从而获得企业所需资本和创造财富的机会。
经典文化创业理论的作用机制明确地把创业活动和财富创造与对文化的合适利用联系起来,通过把企业家概念化为“技术娴熟的文化经营者”来加强组织理论中战略(独特性)和制度视角(合法性)之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联系,使文化和文化过程成为理解“文化作用被边缘化的经济视角所主导的创业研究领域”的中心,表明了文化、制度和身份理论的新发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新创企业如何获取资源和创造财富,具有重要的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
(二)文化创业理论作用机制的演进
1. Garud等(2014)的文化创业理论作用机制
Lounsbury和Glynn(2001)构建的理论框架中,明确提出创业讲故事是新创企业获得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支持的一种有效手段,并且注意到故事通过设定未来的期望激发了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然而,他们的研究将讲故事与合法性身份获取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固定关系——一旦讲述的故事能在最初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那么随后必将会源源不断地获得其所赋予的组织合法性。可现实并非如此。例如,许多创业项目在最初会因其所描述的美好蓝图(创业计划书)吸引到风险投资商的A轮投资,但是却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造成实际与设想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而失去了风险投资商B轮的追加投入。也即是说,创业故事与合法性身份之间是一个动态的相互调整且不断适应的关系。为填补这个研究缺口,Garud等(2014)借鉴“期望社会学”的研究成果(Brown等,2000;Brown和Michael,2003),对经典的文化创业理论框架进行了修正,如下图2所示。
与经典理论框架相比,Garud等(2014)依然是围绕讲故事作为企业合法化的核心机制展开分析,但故事内容的吸引力是通过设定未来期望获得的,补充了原有框架中故事内容的吸引力来源;同时,该理论框架突出了一个悖论,即通过投射性故事为获得企业合法性而设定的期望也可能成为未来失望的根源,需要通过重新修订故事来重获企业合法性,这突出了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创业故事的构建过程。Garud等(2014)的理论作用机制表明了创业是一个持续构建和重新构建未来的愿望和过去事件的过程,创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探讨了合法性的动态属性,通过修订故事来维持或重新获得合法性具有可能性;补充了早期的文化创业研究工作,并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设定期望以获得合法性、维持合法性或恢复合法性。
2. Lounsbury等(2019)的文化创业理论作用机制
在文化创业理论提出之后的第20年即2019年,Lounsbury等(2019)总结性地回顾了文化创业理论近20年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一个扩展的文化创业理论框架(见图3)以对其早先提出的框架进行完善。
Lounsbury等(2019)在该框架中延续了讲故事是文化创业研究工作的核心特征的观点,但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扩展。
文化创业理论是在创业研究出现“语言转向”的背景下诞生的,并且以编纂和讲述创业者或新创企业的故事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因此其研究先天地借鉴了语言学的方法,更好地用于分析创业中的身份构建和合法性资源获取等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叙事分析方法(王辉,2015;张慧玉和程乐,2017;杜晶晶等,2018)。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案例分析的形式。叙事分析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其目的在于回应人们的各种行为与需要,力图抓住特定时空中个体行为的微妙差别与丰富内涵(王辉,2015)。常见的叙事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叙事的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和叙事性分析(narrative analysis)(Polkinghorne,1995)。前者运用范式性思维进行分析,后者运用叙事性思维进行分析(杜晶晶等,2018)。
创业叙事分析则是“对创业者讲述故事的分析”(Gartner,2007)。故事是创业叙事分析的基础素材,这已为广大研究者所接受。叙事分析将创业故事放置于更大的语境中,赋予了不同学者从自身角度解读同一故事的机会,这使得创业叙事分析同时具备了分析价值和创造价值(王辉,2015)。
与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相比,叙事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克兰迪宁和康纳利,2008;王辉,2015):第一,聚焦个体经验的探究。创业叙事分析的对象通常是单一的新创企业或创业者个体;第二,强调事件、情境与过程的深描。创业叙事分析提倡对个体创业过程所赖以产生的环境和情境特性进行详尽地描述;第三,追求分析性的理论构建。创业叙事分析从故事的讲述分析中构建理论框架,尽管在信效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却能使读者对创业本质有所洞察和领悟(Gartner,1993)。
虽然文化创业理论的研究主要以基于案例形式的创业故事的叙事分析方法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量化实证研究方法是排斥的。从前面的文献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实证研究文献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公开发表。由于文化创业研究涉及文化和情境因素,存在大量的非结构化描述数据,一般需要通过定性的分析方法进行编码和转化为结构化数据,才能进行定量分析。因此,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大多数使用结合定性叙事分析和定量假设检验的混合方法,尽管具有较大的难度和工作量。
五、文化创业理论的研究边界文化创业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理论体系,其研究边界在持续的扩展之中(Lounsbury和Glynn,2019)。在继续关注核心的创业研究领域的同时,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了最优区分、公司治理等其他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
(一)文化创业理论的核心研究边界
文化创业理论始终将创业活动作为核心的研究领域。不过,在萌芽期,文化创业理论主要被用于研究社会企业的社会创业问题;进入发展期之后,文化创业理论更多地被用于制度创业、创业失败等创业热点问题。
1. 文化创业与社会创业
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不同,其旨在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实现社会价值创造的目的,在获取外部资源时有着更高的难度(厉杰等,2024)。社会大众及利益相关者对社会创业者的期望是模糊的,认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难以预测的(Waldron等,2016),因此创业者只有释放清晰且有价值的信息构建合适的创业身份,才能说服外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Suddaby和Greenwood,2005)。社会企业如何突破“合法性”障碍,获取所需的社会资源并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社会创业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Ruebottom,2013)。而文化创业理论运用讲故事等手段获取合法性资源的机制同样适用于社会创业实践。
Margiono等(2019)运用印尼和英国两家社会企业的创业案例研究,考察了在社会创业背景下讲故事如何获取创业合法性的过程,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反映完整的作用机理。该分析框架表明:在社会创业过程中,故事的主人公、受众的熟悉程度、故事情节以及所使用的媒介都会在社会企业向外界的叙事性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此影响着其合法性获取行为。关于故事主人公的“人设”和特征,Ruebottom(2013)认为要将主人公与对手进行比较,设置成对抗性“人设”特征,如英雄与恶棍、开拓者与保守者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通过烘托一种紧张对立的气氛,突出主人公的积极性与反对者的消极性,使受众更倾向于赋予主人公组织合法性的判断。关于故事的叙事性表达和传递,采取有效的修辞策略很关键。刘志阳和许莉萍(2020)从故事受众的角度提出:社会创业者面对政府人员时应采取愿景化修辞策略,面对公益创投机构时应采取隐喻性修辞策略,面对内部员工时应采取基于价值的修辞策略,面对志愿者时应采取基于情感的修辞策略。邓晓辉等(2018)则从制度环境的视角探讨了可以采取的修辞策略。他们发现,当制度环境稳定时,企业可以采取遵循的修辞策略、回避的修辞策略或遵循与回避相结合的修辞策略来获取合法性;当制度环境不稳定时,企业可以采取批驳的修辞策略、架构的修辞策略或象征性遵循但实质性架构的两面策略来获取合法性。
2. 文化创业与制度创业
制度创业本质上就是行为主体通过不同的战略手段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改变现存制度或创建新制度的过程(李雪灵等,2015)。对制度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劝说现有体制下的行为者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并愿意投身于其中。这可以运用文化创业理论通过搜集、叙述具有相关性及象征意义的故事,传播主张变革的观念,以改变现有制度秩序(Greenwood等,2002;张慧玉和程乐,2017)。为了提高新建制度逻辑上的合法性,行为者可运用多样化的叙事风格(如悲喜剧、浪漫主义、反讽等)将故事内容与特定组织、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以此来获得受众关注、强化其对新建制度的接受和认同(Wright和Zammuto,2013)。按照Greenwood等(2002)的观点,一个完整的制度创业过程可以划分为震荡、去制度化、前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化、加强制度化六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属于创建变革基础阶段,第四个阶段属于理论化新制度阶段,最后两个阶段属于扩散化新制度阶段(项国鹏和阳恩松,2013)。文化创业讲故事在不同的阶段有着相应的特点,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1)创建变革基础阶段。这一阶段是为正式的制度变革提供思想准备的过程,此时讲述故事的目的是描绘变革愿景,让成员认识到变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Zilber,2007;Ruebottom,2013)。(2)理论化新制度阶段。这一阶段是将思想和认知中的新制度的美好愿景抽象化、结构化、条文化、规范化,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过程,此时讲述故事的目的在于明确变革方案,突出新制度的优越性,促进联盟的构建和新制度的传播(Munir和Phillips,2005)。
3. 文化创业与创业失败
创业失败是创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因为绝大多数创业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少部分佼佼者能创业成功。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有些创业者经历了创业失败反而“愈挫愈勇”,而另外一些则“一蹶不振”(Politis和Cabrielsson,2009)?Cardon等(2011)指出,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不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会对创业者面对失败所做出的归因以及后续决策等行为产生差异性的作用。而文化创业作为一种娴熟运用文化工具进行意义建构的活动,可被创业者应用于对创业失败的叙事中以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失败归因以及后续创业绩效的。
有学者提出,可以从创业失败故事讲述的内容上区分两种失败归因——缺少运气和犯了错误(Cardon等,2011))。其中,缺少运气反映的是将创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非创业者所能掌控的外部环境等外因,而犯了错误则反映的是将创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创业者的能力和经验等内因。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事实上都会出现创业失败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企业的污名化、创业者的声誉受损、资金的撤出等。然而,通过创业失败归因叙事的意义建构却可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例如,如果人们认为创业失败的原因是情有可原、能够接受的,那么创业者就会发现能够相对容易地继续得到风险投资者的资金支持以实现“东山再起”;而如果人们认为此次的失败是咎由自取、不可饶恕的话,那么企业将被彻底打上污名的标签,创业者也很难立足于社会。通过对创业失败故事讲述内容的有意识的组织,可以形成缺少运气和犯了错误两种不同的归因:如果创业失败故事更多的是讲述有关市场力量、时间约束、机构支持等内容时,则指向的归因类型是缺少运气的外因;如果创业失败故事更多的是讲述有关商业模式、管理能力和经验、创新等内容时,则指向的归因类型是犯了错误的内因。不管创业失败故事讲述的具体内容如何,都需要结合具体的文化情境构建符合利益相关者的创业身份意义以减少失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晓宇和蒲馨莲,2018)。Mantere等(2013)识别了七种不同类型的具体叙事归因——宣泄、傲慢、时代精神、背叛、报应、机械的和命运,并分别界定了每种叙事类型所属的失败归因及其功能。
(二)文化创业理论的扩展研究边界
文化创业理论创立的初衷是将文化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通过运用讲故事的方式构建创业者或新创企业的身份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支持,从而动员和获取创业成长所需的各种资源。随着该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其研究边界还逐步地扩展到了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等相关研究领域。
1. 文化创业与最优区分
企业一方面为了获得组织合法性,必须要与既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保持一致(DiMaggio,1982;Suchman,1995);另一方面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寻求独特的战略定位以建立持续竞争优势,必须要具备独特的核心能力和战略性资产(Barney,1991)。Deephouse(1999)将这一悖论形象地称之为“求同还是存异”问题。在战略领域,该问题体现为企业的最优区分战略选择(Zhao等,2017)。其中,运用讲故事或叙事的方式向外界宣称合法且独特的组织身份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认同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策略(郭海等,2020)。Navis和Glynn(2011)指出,身份能够同时兼具合法性和差异性的特征,并且赋予了组织一定的区分度和归属感。讲故事是一种建立和宣示身份的常用手段,倘若连贯一致的故事能够突出企业特色属性,并引发利益相关者的共鸣,组织便能获取相应的合法性资源(Garud等,2014)。
通过故事叙事能够实现最优区分的根本原因在于类别的独特性,独特的类别既能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重要的差异性来源,又能够吸引那些高度重视创新性和新颖性的受众(Taeuscher 等,2022)。类别塑造了受众的评估,因为它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可以在正式评估之前轻松地预选一组考虑因素;类别也会影响受众的评估,因为它是感知组织一致性和独特性的认知锚(Zhao 等,2017)。所以,类别在实现最优区分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Younger等(2025)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在不同的市场类别阶段受众兴趣和期望的变化如何影响其对最优区分的判断。他们认为这种判断取决于故事主角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主角被视为正确类型的演员(企业的角色认同),以在情境化的理解框架(认知参照物)内解决特定类型的紧张局势(不确定性考虑)。Taeuscher等(2022)通过对美国爱彼迎(Airbnb)45个类别
2. 文化创业与公司治理
将文化创业理论应用于公司治理研究的学者是Park和Zhang(2020)。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公司主动跨越国界在外国资本市场上市。这些公司一方面需要遵守东道国监管的要求,包括要求它们根据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采取新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需要与母国的文化制度保持一致。公司在国外上市决策本质上就是创业决策,即公司冒险进入外国资本市场,筹集金融资源,并获得市场专家的认可,以实现其未来增长的目标。为此,两位学者提出了全球框架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公司治理中的文化创业机制。在此机制中,外国上市公司针对东道国投资者量身定制其叙事。基于文化创业的研究成果,Park和Zhang(2020)对境外上市公司如何融入全球框架,为东道国投资者提供个性化治理实践的叙事进行了理论分析。除此之外,他们还实证研究考察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独立董事在母国和东道国对其角色认知存在差异时,对其资源提供角色的监督的相对重视程度。研究发现,当独立董事缺乏在其母国实施独立董事作为监督者的既定理念的能力时,全球框架在东道国获得投资者认可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
Park和Zhang(2020)的开创性研究有助于新兴的关于公司治理越轨和创新等问题的深入探讨,揭示出了文化创业战略作为一种理想的潜在理论机制,它是在单一公司层面甚至在同一国家内观察到的治理偏差的基础。然而,在两位学者的研究之后并没有针对单一企业公司治理的后续研究出现,因此文化创业理论是否是解释单一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差异的基础的论断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一)研究结论与贡献
针对当前文化创业文献呈现碎片化态势、缺少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国内学术界对此理论还不够重视、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等问题,本文对自2001年由Lounsbury和Glynn创立的文化创业理论的完整体系和研究成果进行了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结果表明,文化创业理论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并通过融合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和组织认同方法,对战略和组织领域的创业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研究范围从经典的创业领域延伸到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新兴领域,研究对象从营利性企业跨越到非营利性社区基金会(例如,Graddy和Wang,2009)、孵化器(例如,Tracey等,2018)、众筹平台(例如,Jancenelle等,2019)、道德市场(例如,Hedberg和Lounsbury,2021)、贫困环境(例如,Kimmitt等,2024)等,研究目的从专注于资源获取和财富创造扩展到更一般的非经济领域的价值创造。这些为文化创业理论的普适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研究层次更加多元化——从最初理论所关注的讲故事的个体层面的分析,上升到接受对制度领域内或跨领域的分布式、集体讲故事的理解,为不断发展的创业身份和创业可能性提供了发展空间。再次,文化内涵得到了新发展,文化资源也被概念化为制度逻辑、框架、词汇、类别、修辞、故事、叙事、话语、沟通等等(Thornton等,2012;Giorgi等,2015;Vaara等,2016),促进了对“文化作为元素的工具集”的更广泛的理解,可以让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下创造性地运用和部署文化。最后,学者们更加明确地强调了文化创业过程的迭代和递归关系,这更有力地将文化创业根植于文化背景之中并动态地构建文化环境。
(二)研究问题和不足
如同任何一门新兴的理论一样,文化创业理论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范围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和值得探讨的地方。
第一,从研究内容上看,如何通过创业故事的讲述来构建特定的创业身份以获取组织合法性是当前文化创业理论的核心作用机制(倪宁和李钊仪,2016;Lounsbury和Glynn,2019)。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创业故事的微观结构(倪宁和李钊仪,2016);创业故事讲述的意义和目的(Beckert,2016;Lounsbury和Glynn,2019);创业故事作为自变量与合法性获取以及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路径(Überbacher,2014;武守强和冯云霞,2018)。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是:(1)虽然我们清楚了一个完整的创业故事是由创业身份阐释、合法化身份的意图和劝说修辞运用三个构面所组成(倪宁和李钊仪,2016),但是不同的创业故事之间的差异性如何体现?其差异化程度又该如何有效衡量?简而言之,即创业故事概念的操作化问题。这对于文化创业研究从方法上由当前的定性叙事研究为主向更加多元化的定量实证研究发展至关重要。(2)Lounsbury和Glynn(2019)指出,创业故事的讲述在文化创业的理论框架中是既可以作为自变量也可以作为因变量而存在的。当其作为自变量时,要探讨的是创业故事对组织合法性获取以及身份构建的作用机制;当其作为因变量时,要考察企业资源和制度资本存量,以及其他一些情境因素对创业故事结构、内容讲述方式等的影响机理。显然,既有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前者的理论价值毋庸置疑,后者的实践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那些影响故事讲述具体内容和方式的因素并掌握其中的影响机理,那么就能够有效指导创业者和新创企业根据现有的情境组织好故事的结构和内容并以适合的方式讲述给利益相关者以获得其合法性资源,从而使得文化创业研究从理论探索逐步走向实践应用。
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创业叙事分析正朝着整合、动态、开放的方向演进,为创业研究特别是复杂的研究主题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探讨空间(张慧玉和程乐,2017),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较为成熟且应用最为广泛的还是“叙事的分析”,虽然使用了众多的叙事素材,但研究人员往往只是从不同素材中寻找共性。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叙事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更值得提倡(成伯清,2012)。“叙事性分析”更加注重故事的完整性,而非执着于某些片面的要素,主张通过分散的情节构建生平故事。换句话说,创业叙事研究除了进行理论的归纳之外,还要进行理论的演绎。
第三,从研究边界上看,文化创业理论自提出之日起至今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始终是创业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到最优区分和公司治理等战略与组织研究领域,相应的研究对象也从营利性企业延伸至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形式,但相较于其他新兴理论而言,研究边界仍然比较狭窄。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论发展的独立性和完善性,但另一方面却削弱了理论对实践的强大解释力和影响力,不利于其进一步的推广和深化。Lounsbury和Glynn(2001)就曾指出,“文化创业的核心机制就是通过运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塑造个体或者组织的身份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资源最终实现价值增值,这一机制不仅仅适用于新创企业,同样适用于成熟企业;关注故事的讲述对战略理论和组织理论也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文化创业理论具有很强的张力,凡是涉及构建身份或获取合法性的问题均可以考虑运用或者融入文化创业的理论思想。该理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研究边界和范围仍需要进一步地扩大。
(三)未来研究展望
那么,接下来文化创业理论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呢?在此,我们根据上述理论存在的不足,结合中国文化情境的特征为后续研究者尤其是国内研究者指出几点未来的研究议题。
第一,对文化创业理论的核心要素——故事的讲述及其作用机制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按照倪宁和李钊仪(2016)的观点,故事讲述能否实现预期的身份建构和合法性获取的目标,取决于故事的内容结构、呈现形式和讲述方式。虽然既有文献对故事的这三个方面都分别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Brattström和Wennberg,2022),但是三者之间的匹配关系却未有研究。显然,这三者之间的匹配关系要比这三者本身对于目标的达成更为关键。并且它才是区分不同文化创业活动的标志。这就意味着,要刻画具体的文化创业活动不仅要分别描述故事的内容结构、呈现形式和讲述方式三个方面,还需要对这三者之间的匹配关系加以重点分析。也即是说,后续研究在对创业故事构念进行测量时可以考虑从上述三个方面来选取指标,并以三者之间的匹配关系作为衡量的标准。实际上,真正决定故事如何讲述的因素是受众的认知和需求。毕竟,无论是身份意义的建构还是合法性资源的赋予都是来自受众的理解与支持。Fisher等(2017)指出,要根据利益相关者类别和特征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叙事方式。所以,后续研究在考察创业故事的具体内容特点时要重视对前因变量的探讨,而受众的个体、组织和外部环境等层面的相关因素都会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众多可能的影响因素中,文化环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创业讲故事就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利用手头的文化资源进行的一种有效叙事(Wry等,2011),因此娴熟的文化创业者不仅要深刻领会所处的文化环境,还要善于运用具体的文化资源。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好故事必须在主题和内容上符合人们的文化认同,否则无法被给予理解。而且不论故事采取何种编纂形式和讲述方式,只有它进入了人们的感知、被人们内化后才能真正成为认知的资源。当前文化创业研究更多的是在西方的文化情境下进行的,中国学者开展后续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地移植和复制,而要根据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色进行本土化的创新性探索。
第二,对文化创业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叙事分析法做进一步的转变和交叉融合。首先,从叙事的分析转向叙事性分析,从理论的归纳转向理论的演绎。文化创业理论经过近25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且相对稳定的理论框架体系,逐步从最初的理论构建和归纳阶段走向接下来的理论解释和演绎阶段,以彰显该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为此,其叙事分析方法也要相应地从叙事的分析转向叙事性分析,从对要素和片段的总结转向对完整故事情节的分析。对于研究者来说,既要全面掌握叙事研究的方法,又要在理论构建和情节组织方面达到更高的层次,这样才能从经验中得到普遍性的意义。这需要研究者将自己置身于情境与故事之中,从将来与过往的联系中审视当下,深入地描绘那些生动、微妙、难以捉摸的事件,而非泛泛的阐释性叙述。因此,未来的创业叙事研究应对关注叙事的本质特征及其前因后果,充分利用语言学相关理论(如系统功能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符号学等),对创业问题作出深刻有力的阐释。其次,叙事分析存在主观性较强、普适性较弱的问题,在方法上缺乏独立性。后续叙事分析可以借鉴案例研究的发展路径(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一方面为了克服主观性过强的问题,要运用规范的语言分析技术对文本进行深入、细致、有层次的分析;另一方面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提高研究的规范性,积极与其他成熟的研究方法结合。另外,基于跨学科特征及叙事研究的性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更多地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提高研究的信效度和数据收集的效率,以此推进创业叙事研究方法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第三,对文化创业理论的研究边界做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故事是文化创业理论建立的基石,无论是其始终关注的创业研究领域,还是后续拓展进入的战略研究领域和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均是以考察如何通过故事讲述以建构意义,从而获取合法性资源的完整过程作为文化创业理论应用于该研究领域的典型例证。然而,正如Zimmerman和Zeitz(2002)指出的那样,讲故事并不是文化创业理论所独有的行为;事实上,早在文化创业理论创立之前,讲故事就被应用于战略管理领域(楠木建,2012)和市场营销领域(Stern,1991,1994),以实现特定的战略意图和塑造品牌形象。文化创业理论的出现使得故事的讲述与(合法性)资源获取以及绩效提升之间的作用机制得到了更具普遍性的揭示并被高度重视,这就为文化创业理论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显而易见的是,接下来文化创业理论可以应用于市场营销领域的品牌塑造和推广研究,探讨行动者如何采取有效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向受众传递品牌的价值和意义以赢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除此之外,技术创新领域的新产品上市问题,以及组织学习领域的知识共享与传递问题都可以作为下一步延伸和拓展的考虑对象。
| [1] | 邓晓辉, 李志刚, 殷亚琨, 等. 企业组织正当性管理的修辞策略[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137–155. |
| [2] | 杜晶晶, 王晶晶, 陈忠卫. 叙事取向的创业研究: 创业研究的另一种视角[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40(9): 18–29. |
| [3] | 郭海, 李永慧, 赵雁飞. 求同还是存异? 最优区分研究回顾与展望[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6): 214–224. |
| [4] | 金婧. 印象管理理论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应用: 回顾与展望[J]. 管理学季刊, 2018, 3(2): 113–143. |
| [5] | 厉杰, 李浩瑞, 沈发美, 等. 创业叙事卷入对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4, 36(5): 66–76. |
| [6] | 李雪灵, 黄翔, 申佳, 等. 制度创业文献回顾与展望: 基于“六何”分析框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5, 37(4): 3–14. |
| [7] | 刘志阳, 许莉萍. 求同还是存异: 制度逻辑视角的社会创业者修辞策略选择[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 32(3): 1–12. |
| [8] | 倪宁, 李钊仪. 创业故事的三成分模型: 探索文化创业的微观结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11): 58–70. |
| [9] | 王家宝, 史真, 厉杰. 故事何以成为创业法宝?——文化创业的视角[J]. 清华管理评论, 2021(6): 38–45. |
| [10] | 汪涛, 周玲, 彭传新, 等. 讲故事塑品牌: 建构和传播故事的品牌叙事理论——基于达芙妮品牌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3): 112–123. |
| [11] | 王泽民, 龙静, 张吉昌. 如何讲好你的创业故事?——基于创业叙事微观层面论点的fsQCA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4, 45(5): 105–123. |
| [12] | 武守强, 冯云霞. 修辞视角下组织合法性的话语构建——以中国百胜和麦当劳为案例[J]. 经济管理, 2018, 40(1): 92–108. |
| [13] | 于晓宇, 陈依. 创业中的印象管理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管理学报, 2019, 16(8): 1255–1264. |
| [14] | 于晓宇, 蒲馨莲. 中国式创业失败: 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J]. 管理科学, 2018, 31(4): 103–119. |
| [15] | 张慧玉, 程乐. 创业叙事研究述评与展望[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7(3): 40–50. |
| [16] | 周冬梅, 陈雪琳, 杨俊, 等. 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2020, 36(1): 206–225. |
| [17] | Bolino M C, Kacmar K M, Turnley W H, et al. A multi-level review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 motives and behavio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34(6): 1080–1109. |
| [18] | Brattström A, Wennberg K. The entrepreneurial st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2, 46(6): 1443–1468. |
| [19] | Brown N, Rappert B, Webster A. Contested futures: A sociology of prospective techno-science[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 [20] | Cardon M S, Stevens C E, Potter D R. Misfortunes or mistakes?: Cultural sense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1): 79–92. |
| [21] | Eisenhardt K M, Graebner M E.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1): 25–32. |
| [22] | Escalas J E. Imagine yourself in the product: Mental simulation,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and persuasion[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04, 33(2): 37–48. |
| [23] | Fisher G, Kuratko D F, Bloodgood J M, et al. Legitimate to whom? The challenge of audience diversity and new venture legitimac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1): 52–71. |
| [24] | Foss N J, Klein P G. Organizing entrepreneurial judgment: A new approach to the firm[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 [25] | Foss N J, Klein P G, Bjørnskov C. The context of entrepreneurial judgment: Organizations,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9, 56(6): 1197–1213. |
| [26] | Gartner W B. Words lead to deeds: Towards an organizational emergence vocabular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3, 8(3): 231–239. |
| [27] | Gartner W B.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 and a science of the imagin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7, 22(5): 613–627. |
| [28] | Garud R, Schildt H A, Lant T K. Entrepreneurial storytelling, future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legitimacy[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4, 25(5): 1479–1492. |
| [29] | Gehman J, Soublière J F.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making culture to cultural making[J].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 Management, 2017, 19(1): 61-73. |
| [30] | Giorgi S, Lockwood C, Glynn M A. The many faces of culture: Making sense of 30 years of research on culture in organization stud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5, 9(1): 1–54. |
| [31] | Graddy E, Wang L L. Community foundati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apital[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9, 38(3): 392–412. |
| [32] | Greenwood R, Suddaby R, Hinings C R. Theorizing change: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field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1): 58–80. |
| [33] | Hedberg L M, Lounsbury M. Not just small potatoes: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moralizing of market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1, 32(2): 433–454. |
| [34] | Johnson V. What is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founding of the Paris Oper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3(1): 97–127. |
| [35] | Kimmitt J, Kibler E, Schildt H, et al. Place in entrepreneurial storytelling: A study of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a deprived contex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4, 61(3): 1036–1073. |
| [36] | Lounsbury M, Gehman J, Glynn M A. Beyond homo entrepreneurus: Judgment an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9, 56(6): 1214–1236. |
| [37] | Lounsbury M, Glynn M A.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Stories, legitimac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7): 545–564. |
| [38] | Lounsbury M, Glynn M A.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 [39] | Mantere S, Aula P, Schildt H, et al. Narrative attributions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4): 459–473. |
| [40] | Margiono A, Kariza A, Heriyati P. Venture legitimacy and storytelling in social enterprises[J]. Small Enterprise Research, 2019, 26(1): 55–77. |
| [41] | Munir K A, Phillips N. The birth of the “Kodak moment”: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5, 26(11): 1665–1687. |
| [42] | Nagy B G, Pollack J M, Rutherford M W, et al.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 credentials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behaviors on perceptions of new venture legitimacy[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36(5): 941–965. |
| [43] | Navis C, Glynn M A. Legitimate distinctivenes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 Influence on investor judgments of new venture plausibil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3): 479–499. |
| [44] | Park S H, Zhang Y L.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diffusion: Framing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by U. S.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0, 31(6): 1359-1384. |
| [45] | Politis D, Gabrielsson J. Entrepreneurs’ attitudes towards failure: An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09, 15(4): 364–383. |
| [46] | Ruebottom T. The microstructures of rhetorical strategy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uilding legitimacy through heroes and villain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1): 98–116. |
| [47] | Stern B B. Who talks advertising? Literary theory and narrative “point of view”[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1, 20(3): 9–22. |
| [48] | Stern B B. Classical and vignette television advertising dramas: Structural models, formal analysis, and consumer effect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4, 20(4): 601–615. |
| [49] | Taeuscher K, Zhao E Y, Lounsbury M. Categories and narratives as sources of distinctiveness: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within and across categor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2, 43(10): 2101–2134. |
| [50] | Tracey P, Dalpiaz E, Phillips N. Fish out of water: Translation, legitimation, and new venture cre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61(5): 1627–1666. |
| [51] | Überbacher F. Legitimation of new ventures: A review and research programm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4, 51(4): 667–698. |
| [52] | Waldron T L, Fisher G, Pfarrer M. How social entrepreneurs facilitate the adoption of new industry practi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6, 53(5): 821–845. |
| [53] | Wright A L, Zammuto R F.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Colonel and the Cup in English County Cricket[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1): 51–68. |
| [54] | Wry T, Lounsbury M, Glynn M A. Legitimating nascent collective identities: Coordinating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 22(2): 449–463. |
| [55] | Younger S, Preedom J, Navis C. Legitimately distinct entrepreneurial stories in evolving market categor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5, 40(1): 106436. |
| [56] | Zhao E Y, Fisher G, Lounsbury M, et al.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Broaden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1): 93–113. |
| [57] | Zilber T B. Stories and the discursiv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Israeli high-tech after the bubble[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7, 28(7): 1035–105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