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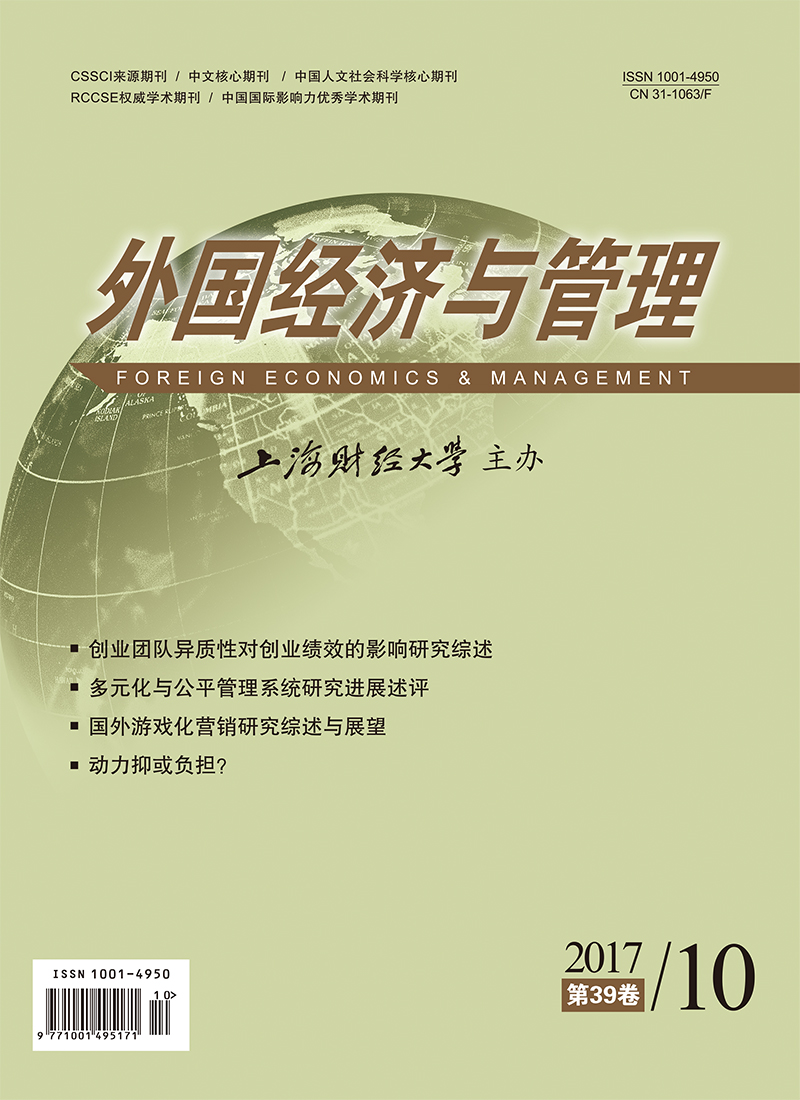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年39卷第10期 |
- 汪金爱, 李丹蒙
- Wang Jin’ai, Li Danmeng
- 高管团队动力研究述评——基于高阶梯队理论过程模型
-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op management team dynamics: based on the process model of upper echelon theory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10): 53-71
-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7, 39(10): 53-71.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6-1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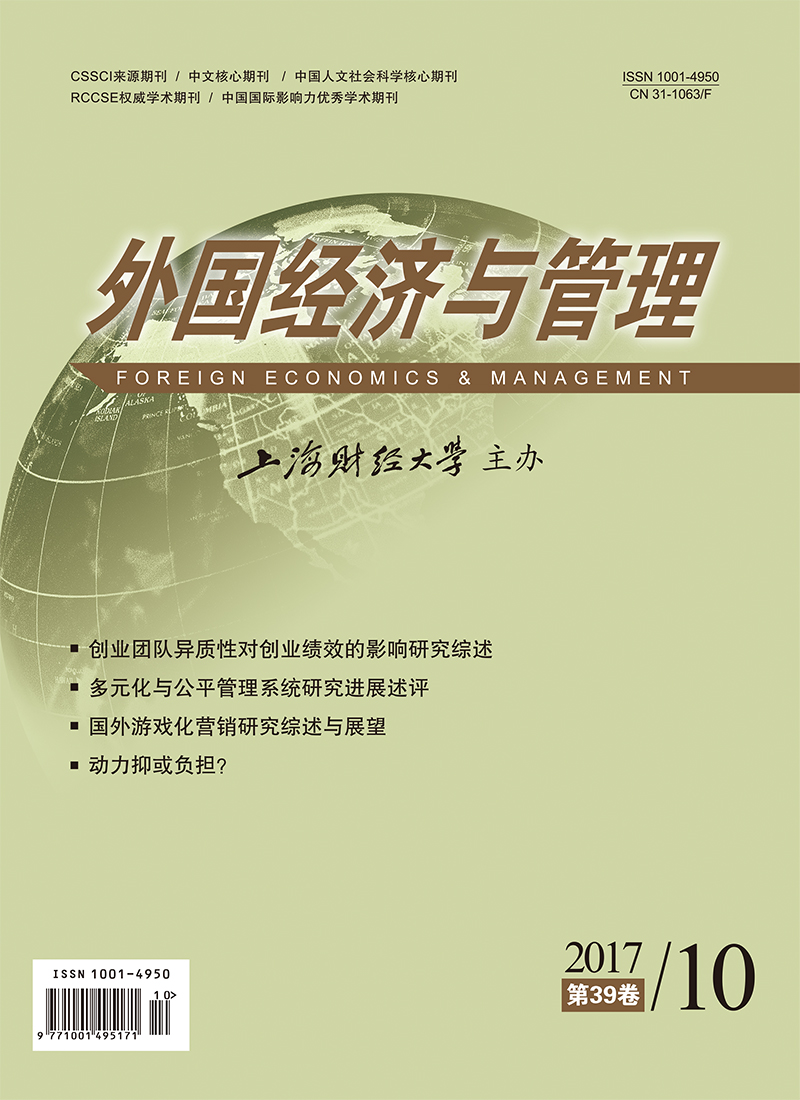
2017第39卷第10期
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简称高管团队)控制着公司的战略方向并影响公司经营绩效,是公司活动中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群体。高阶梯队理论注意到了团队的重要性,认为公司战略不仅事关CEO等高管个人,也是他们所领导的高管团队特征的一种“反映”(Hambrick和Mason,1984)。该理论对于公司战略行为的强大解释力加之数据获取较为方便,极大地促进了高管团队行为及其组织影响的研究,高管团队由此成为战略管理领域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Finkelstein等,2008)。
然而,高阶梯队理论以人口学背景变量等替代高管个人或者团队的潜在心理特征,尽管极大地方便了数据获取,却由于间接度量以及过长的因果链条造成难以解释的“人口学背景黑箱”,因而备受挑战(Priem等,1999;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更为严重的是,高管团队研究一方面强调其与普通工作团队的不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利用成熟的工作团队理论来解释高管团队运作。大量基于“浅层”人口学背景变量的团队构成或结构方面的实证研究,无一例外地通过“假定”的团队过程来解释其组织影响,高管团队的内部运作以及影响机制掩盖在“过程黑箱”之中,团队过程及动力学研究因此成为完善高阶梯队理论的关键所在(Carmeli等,2011)。如果不从过程和团队动力的角度考察高管团队构成及其结构特征,无论是高管团队异质性还是相互依赖性的结构特征最终都会出现类似的“黑箱”问题(Priem等,1999;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
为此,本文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中的高管团队过程模型,将团队构成、团队结构以及团队过程统一到广义高管团队动力模型之中,一方面,高管团队构成和结构作为输入变量影响团队过程或者过程维度,另一方面,它们作为团队动力过程的结果也受到团队输出变量的影响而在不断变化之中(Forsyth,2013;Mathieu等,2008)。但要深入“过程黑箱”了解高管团队运作并构建真正的高管团队理论,则需要深入到团队过程这一“狭义的”高管团队动力之中。基于这一框架,我们对国内外高管团队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发现既存在大量实证研究的“成熟区”,也存在重要的研究机会的“潜力区”,因而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相应建议。
本文既是对当前快速发展的高管团队研究的一次系统性梳理,也是响应“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之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号召,深入到“群体生活的核心”和“领导力”来了解创造“美好世界”的高管团队运作及其战略影响(Forsyth,2013)。只有深入理解团队动力以及战略决策过程,才能在实践层面为提升高管团队战略领导力提供帮助(Peterson等,2003;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当前,全球经济的长期衰退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人们更加期待“伟大”的领导者及其带领的高管团队,高管团队研究具有时代紧迫感和重要的现实意义(Quigley和Hambrick,2015)。高管团队动力研究旨在揭示企业战略这一“宏观”问题的微观机制,也将成为快速发展的“微观基础运动”(microfoundations movement)在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前沿领域(Felin等,2015;Powell和Rerup,2016)。
二、高管团队动力研究框架大量研究表明,高管团队而非高管个人对组织功能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Finkelstein等,2008),即使在新创企业中,企业管理通常也是高层管理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Ensley等,2002)。动荡和复杂的外部环境导致CEO及董事长面对的任务极具挑战性,高管团队因此成为了一种有效应对手段(Carmeli等,2011;Ensley等,2002)。高管团队可以孕育创新观念并激发出多种决策方案,高层管理者从而能够利用不同的经验应对棘手问题,同时也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增加高管团队的参与和承诺,提高战略执行力(Finkelstein等,2008)。
高管团队的核心要素包括团队构成、团队结构、团队过程(Finkelstein等,2008)。团队构成指团队成员的集体特征,如来自人口学背景的高管经验,包括年龄、资历、专业、教育以及心理因素包括价值观、认知基础、人格等,大部分实证研究集中于团队构成的多样性特征,也即团队异质性(Hambrick等,2015;Mathieu等,2014)。团队结构则由成员角色以及成员间的关系所定义,核心是团队成员角色的相互依赖性。团队构成尤其是团队异质性研究结论的相互矛盾或不一致引发了对团队结构的关注,研究发现成员间相互依赖性的不同会影响高管团队构成多样性的作用(Hambrick等,2015)。团队结构可按照任务、层级、共同成就等划分为水平、垂直、报酬三种依赖性(Hambrick等,2015);依据家族参与程度可将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分为家长式、家庭式、非家族式团队结构(Ensley和Pearson,2005);中国情境中的“差序格局”特征也是常见的家族团队结构形式(姜定宇和鄭伯壎,2014;王明琳等,2014)。
高管团队过程是指团队成员在战略决策中的互动属性,集中表现在社会整合和共识两个维度,其中团队凝聚力是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因素(Finkelstein等,2008)。冲突研究也成为了高管团队过程较为重要的关注点,如认知冲突和情感冲突,前者又被具体化为观念冲突或任务冲突,而后者则包括关系冲突或人际冲突(Ensley和Pearson,2005;Ensley等,2002)。Finkelstein等(2008)认为,团队的组成、结构、过程影响着战略决策过程中的高管团队社会构成和互动,进而影响到战略决策过程从而引起组织结果差异。除了成员间复杂的互动,战略决策也受组织内活动和环境的影响,成为了高管团队战略决策影响的情境因素。基于此,Finkelstein等(2008)提出了高管团队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其核心正是围绕团队互动过程,并认为高管团队研究主要关注三大问题:(1)高管团队内部互动的本质是什么,(2)情境条件如何影响高管团队,(3)高管团队对于战略决策和组织结果的影响如何。

|
| 资料来源:Finkelstein等(2008)。 图 1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高管团队动力研究框架 |
本研究以这一框架为基础,将团队的构成、结构以及过程作为广义范畴的高管团队动力研究核心,而将团队过程作为“狭义”的高管团队动力:高管团队的构成与结构影响团队过程,同时在团队互动过程之中也会导致团队构成与结构发生变化。尽管团队的构成与结构主要体现某一时刻的静态特征,但从高管团队以及企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它们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它们既是团队过程重要的输入变量,也会受到战略决策过程的影响,成为团队的输出结果。因此,本文提出新的动态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针对其中的高管团队构成、结构以及过程,本研究将高管团队动力研究划分为三大类别。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注: 表示已经存在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的领域, 表示已经存在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的领域, 表示研究较少或存在较大研究潜力的领域。
图 2
高管团队动力研究分类框图及研究机会示意 表示研究较少或存在较大研究潜力的领域。
图 2
高管团队动力研究分类框图及研究机会示意
|
第一类研究最受瞩目,通过高管团队构成、团队结构等静态特征来考察他们对公司结果的影响,如国际化战略、战略变革、创新承诺、竞争性行动等。这类研究普遍假定高管团队特征尤其是特征差异会反应到团队过程之中,从而影响组织的不同结果,团队过程或动力成为假想中的中介机制,但很少进行直接检验;团队异质性研究通常也假定高管团队内部存在频繁互动从而共同进行战略决策(Hambrick等,2015)。如将团队任期作为团队凝聚力的代理;教育程度多元化作为团队内认知多元化的替代,并与全球性战略姿态相关联;高管团队规模反映了处理复杂信息的集体能力因而提升了国际化水平等(Finkelstein等,2008)。基于人口学背景的团队异质性成为这类研究的热点,通常假定背景多样性会带来更多的观点和认知差异,从而提高决策质量,然而这些预设关系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检验。部分学者也对团队异质性研究中成员间频繁互动的团队结构假设提出质疑,认为团队结构存在很大差异,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并不相同,基于角色依赖的团队结构研究开始出现,部分缓解了团队异质性研究的困境(Barrick等,2007;Hambrick等,2015)。
第二类研究聚焦于团队过程的某一维度,通过直接测量过程变量来缓解第一类研究产生的“黑箱”或者“因果间隔”问题(Priem等,1999;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但这类研究目前关注的过程维度较为有限,Finkelstein等(2008)重点讨论了两个维度,即社会整合和共识。社会整合概念(O’Reilly等,1989)来自于Shaw(1981)的团队凝聚力,通常代表成员间相互吸引的情感成分,是预测群体行为和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Ensley等,2002;Michalisin等,2004)。Hambrick(1994)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为宽广的行为整合(behavioral integration),成为高管团队研究的新热点(Carmeli等,2011;Ou等,2014)。这类研究的缺点是仅仅聚焦于团队过程的有限维度,并未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距离“真实”的战略决策过程仍有距离。
由此产生第三种类别,即直接研究高管团队的战略决策过程和决策风格,探讨他们的形成因素并检验对企业绩效等组织结果的影响。这类研究往往需要较为创新的研究方法,如利用Q方法开展高管团队决策研究以及采用案例等质性或混合研究方法(Peterson等,2003;Wong等,2011)。这类研究弥补了以上两类研究的不足,但由于研究难度的增加以及度量的困难,大多局限于小样本以及质性研究的描述性分析之中。与其他研究相比,这类研究仍然处于前期的探索性研究阶段,但其研究过程真正触及了狭义高管团队动力,成为未来团队动力研究的新方向(Wong等,2011)。
三、高管团队构成与结构研究(一)高管团队异质性
高管团队异质性备受关注但却是最为模糊的团队特征,团队异质性与组织结果之间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实证结果经常出现(Finkelstein等,2008;Hambrick等,2015;Nielsen,2010)。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人口学背景作为高管成员经验广泛性的度量,其异质性程度也代表着认知多样性(Hambrick和Mason,1984;Priem等,1999),但时至今日,并没有研究直接检验这种关系(Finkelstein等,2008);即便如此,背景多样性也只有在团队需要认知多样性时,才会由于更多的任务相关信息而促进企业绩效(Kearney等,2009)。团队异质性研究的热潮,主要来自于人口学背景变量的易获性、客观性以及可靠性,但其潜在意义却受到了质疑(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除此之外,这类研究还忽略了高管团队的其他重要的特征,如权力分布、时间、规模、文化以及团队结构等情境因素(Hambrick等,2015;Nielsen,2010)。如果权力分布极不均匀,如存在强势CEO或董事长,背景异质性高可能并不代表团队的认知多样性。
高管团队异质性也成为了国内研究的主流,重点考察团队浅层人口学背景异质性与特定的战略选择(如国际化、创业精神、创新等)以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团队异质性的种类以及在不同文化与制度背景中团队多样性的组织意义。如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中,学者们对团队规模、教育水平及任期等一般性特征(贺远琼等,2009;孙海法等,2006)、女性加入高管团队(曾萍和邬绮虹,2012;任颋和王峥,2010)、多种团队异质性的同时作用(胡望斌等,2014;姚冰湜等,2015)等进行了实证检验。除公司绩效外一些重要的战略变量也用来检验高管团队的影响,如多元化(鲁倩和贾良定,2009)、创新(肖挺等,2013)、企业并购(杨林和杨倩,2012)、企业社会责任(孟晓华等,2012)、创业精神(蒋春燕,2011;杨林,2013)、国际化(薛有志和李国栋,2009)、高管离职(张龙和刘洪,2009)、会计策略(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刘永丽,2014)等。
与国外研究类似,实证结果证实了高阶梯队理论的预测,即高管团队特征也会反映在公司战略决策中,成为影响战略选择和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Finkelstein等,2008;贺远琼等,2009;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但国内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研究大多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谨慎的拓展,有关中国情境独特的背景特征如政商关系、家族关系、地区差异、国有企业等异质性表现则很少涉及,削弱了团队多样性在中国情境中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背景特征正在出现或者原有的背景数据获取变得更为容易,团队异质性研究还将继续增加,这也为更多深层次的异质性构建奠定了基础。
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学背景异质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负面影响甚至没有显著影响(Hambrick等,2015;Nielsen,2010;贺远琼等,2009)。两种对立的理论解释了这种不一致,即信息决策观和相似性—吸引力观(Homberg和Bui,2013)。基于认知多样性理论的信息决策观认为,团队内信息交换和处理方式决定着决策质量,团队异质性引入了更多的决策信息以及更广阔的视角因而增强了决策质量,因此产生积极的组织结果。人口学异质性作为认知多样性的替代,可以促进创新性(Talke等,2011;肖挺等,2013)、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信息源及观点的多元化(Carpenter,2002;贺远琼等,2009)、变革开放性以及挑战和被挑战意愿的增加,这些正向效应导致了积极的战略选择和优异的组织绩效(Horwitz和Horwitz,2007;Nielsen,2010)。基于社会身份理论中的相似性—吸引力观则认为,团队内人们更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相处,因此背景异质性削弱了团队功能,如降低了高管团队内的凝聚力,导致冲突增加、协调成本上升、沟通频率降低、削弱了注意力聚焦、降低了群体认同和凝聚力,因而与团队和组织绩效负相关(Homberg和Bui,2013;Horwitz和Horwitz,2007)。
除了对立的理论差异之外,多种因素可能导致高管团队异质性研究的不一致。首先,团队多样性存在多种类型,要理解团队异质性的不同效应,需要对其进行具体分类,Horwitz和Horwitz(2007)根据团队任务的相关性等划分了生物—人口学背景异质性与任务相关背景异质性,前者如年龄、性别、种族,后者则包括职业背景、教育程度、任期等。其次,研究方法与团队异质性、结果变量等的度量问题。研究方法上多层分析、质性研究以及混合研究方法可以获得更为深入的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存在着多种度量方法,如职业背景多样性可用不同的方法度量其主导职业或者人际职业异质性,它们对组织结果的影响并不相同(Bunderson和Sutcliffe,2002)。第三,情境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许多研究指出不同的作用情境影响高管团队异质性效应(Horwitz和Horwitz,2007;Nielsen,2010)。高管团队的生命周期、规模、企业发展现状、公司内的权力结构等都会影响不同维度异质性与组织结果的关系。如在团队发展的早期异质性负向影响团队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逐渐变弱,甚至变得积极(Chatman和Flynn,2001)。高管团队中如果董事长或者CEO的权力过于集中,即使是与任务紧密相关的背景异质性也可能被更深层次的其他因素所影响,因而也退化为“表层”异质性(Horwitz和Horwitz,2007)。
可见,在没有进行群体过程直接探究的情况下,如果对团队异质性的分类、研究方法与度量以及情境因素不加以关注,有关高管团队背景异质性研究的这种含混不清仍将持续,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组织绩效的特定机制难以得到揭示(Nielsen,2010;Priem等,1999)。未来有关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研究除了扩大异质性的来源如人格等心理学异质性、风险偏好异质性(白云涛等,2007)、文化异质性(Nielsen和Nielsen,2013)及其影响之外,还将继续在以上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同时考察多种异质性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组织结果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Horwitz和Horwitz,2007;Nielsen,2010)。此外,团队异质性在理论层面也具有更为复杂的机制,除了信息决策观和相似性—吸引力观之外,亟待引入其他理论视角进行诠释(Homberg和Bui,2013)。
(二)高管团队结构
高管团队的结构由成员角色以及相互关系所定义,成员角色的相互依赖性是团队结构的核心(Finkelstein等,2008;Hambrick等,2015)。团队规模也是重要的结构特征,团队规模与效能之间的研究由来已久,普通工作团队中规模与团队效能呈曲线或者倒U形关系,团队成员太多或者太少都不利于组织绩效;但这种关系并非在所有团队中都成立,团队规模的正、负效应甚至没有影响在实证中都有发现(Cohen和Bailey,1997)。高管团队研究中通常将团队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如Sanders和Carpenter(1998)认为,团队规模代表着处理复杂信息的整合能力,因而与全球化战略扩展正相关。个别研究探讨了团队规模影响结果变量的中介机制,如Simsek等(2005)发现,行为整合中介了团队规模对绩效的影响,行为整合与规模负相关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团队结构研究的主流集中于成员角色的相互依赖性方面,Barrick等(2007)首先在高管团队结构研究中引入了相互依赖性概念,为高管团队结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Hambrick等(2015)对此进行了理论拓展,并将高管团队相互依赖性定义为高管群体中成员相互影响的程度,这种影响来自于其中的角色和管理机制。并认为高管团队相互依赖性是个多维概念,将其划分为水平、垂直、报酬三种相互依赖性,实证发现三种相互依赖性都显著调节了团队异质性与成员离任和绩效之间的关系(Hambrick等,2015)。Hambrick等(2015)由此推断,忽视团队结构的情境作用是导致异质性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因素。
高管团队结构的相互依赖性也为成对关系(dyad ties)等结构特征研究奠定了基础,高管团队的战略领导力正是通过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CEO或董事长之间的关系实现的,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也体现在对CEO-TMT对接(CEO-TMT interface)研究方面(Bromiley和Rau,2016)。由于团队角色依赖性在创业企业以及家族企业中的重要性,高管团队结构成为了理解创业精神来源以及团队家族性的重要工具。针对家族企业中特殊的家族性特征,Ensley和Pearson(2005)将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划分为家长式(parental )、家庭式(familial)、非家族式(nonfamily),研究发现家族和非家族企业在信息处理、观念(认知)冲突和关系(情感)冲突、群体状态(凝聚力、共享战略共识、群体潜能、冲突)方面均显示了区分效度。两两分析表明,家长式团队与非家族式团队间基本支持了以上结论,但家长式团队却缺少较好的观念冲突。家庭式团队与非家族式团队相比,具有更少的群体潜能、凝聚力、共享的战略共识、更高的关系冲突。说明家长式团队中家族特有的社会整合关系,同时降低了关系冲突和观念冲突,但家庭式团队则削弱了观念冲突而提高了关系冲突。
基于中国情境的垂直组对研究在团队结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是对CEO-TMT对接研究的一种拓展(刘永丽,2014;杨林,2014;张龙和刘洪,2009),如张龙和刘洪(2009)利用高管团队垂直组对关系详细考察了它们对高管离职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情境中董事长的重要性(实际的公司“一把手”),在CEO之外考察了董事长—TMT垂直组对的作用。鉴于中国情境中董事长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并成为实际的“一把手”,董事长—TMT较之CEO-TMT对接研究更为重要。部分国内研究也在相互依赖性范畴内考察了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林浚清等,2003;杨志强和王华,2014)以及高管任期交错(姜付秀等,2013)等较为独特的团队结构特征。学者们注意到中国高管团队结构的独特性,但与异质性研究类似,有关家族关系、政商关联、国有与民营企业等中国情境的团队结构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如中国家族的差序格局特征也会在各类高管团队中反映(姜定宇和鄭伯壎,2014;王建斌,2016;王明琳等,2014)。
高管团队结构研究尽管历史悠久,但也存在将团队结构与团队构成尤其是异质性相混淆的问题,并未聚焦到成员角色的相互依赖性这一核心特征方面。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应该成为未来这一领域探讨的重点,通过成对关系研究在难以介入团队过程的情况下可对高管团队的运作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揭示,这一点对于家族企业、新创企业以及成熟企业中的并购重组、国际化战略、高管解职与继任甚至盈余管理(姜付秀等,2013;薛有志和李国栋,2009)等特殊情境的高管团队研究更有意义。高管团队结构研究也应该关注董事长或CEO与TMT的对接甚至TMT与董事会或中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会影响高管团队的构成、结构甚至团队过程(Bromiley和Rau,2016;Raes等,2011)。
四、高管团队过程研究绝大部分现有的高管团队“过程研究”侧重于对影响团队效能和过程质量的个别维度或元构念进行考察,包括团队凝聚力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社会整合和行为整合概念,工作团队中的传统研究重点团队冲突也不例外。
(一)高管团队凝聚力
凝聚力指“群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Shaw,1981),后续学者将其拓展为成员对团队整体任务或者成员彼此之间的承诺,并认为凝聚力具有人际吸引、任务承诺和群体荣耀三个维度(Mathieu等,2008;Mullen和Copper,1994)。团队凝聚力与绩效关系一直是团队有效性的研究重点,大量研究表明凝聚力对团队绩效有着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关系在团队绩效以行为度量而不是结果度量、效率度量而不是效能度量时更为显著(Beal等,2003;Mullen和Copper,1994)。这种相关性在团队凝聚力的三个维度都显著存在,并且随着团队工作流(teamwork flow)的增加而增强,即越是需要团队协作时团队凝聚力的作用越明显(Beal等,2003;Mathieu等,2008)。
尽管绝大部分群体凝聚力研究局限于组织中较低层级的功能及任务水平团队(Michalisin等,2004),但企业高管团队层面的凝聚力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Smith等(1994)认为凝聚型高管团队像宗族般有效运作,无需在团队维持上花费额外的精力和资源,因而降低了过程损失、增加了群体超常绩效所必需的协同效应。凝聚型高管团队在不确定和复杂环境下,反应速度更快也更灵活,具有更高超的处理问题的技巧(Smith等,1994)。因此,凝聚型团队具有较低的离职率(O’Reilly等,1989),因而团队任期较长从而成为新创企业高绩效运作的重要前提(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0)。同时,高管团队凝聚力与情感冲突正相关而与认知冲突负相关,认知冲突有利于绩效,而情感冲突则不利于团队的有效运作(Ensley等,2003)。Michalisin等(2004)进一步将高管团队凝聚力视作战略性资产,并采用战略资源观和仿真实验方法证明其与高绩效相关;资源观视角及仿真实验方法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高管团队层面的凝聚力与团队绩效的关系研究大多验证了中低层团队中获得的结论,然而高管团队凝聚力研究的独特性还在继续挖掘之中,如不同维度凝聚力对于不同战略决策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凝聚力对于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团队中影响凝聚力的机制研究等都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方向。另外,凝聚力在一些特殊情境中的高管团队,如创业企业与家族企业团队中的作用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王重鸣和刘学方(2007)对于中国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凝聚力研究发现,企业家评价较之中高层管理者评价更容易区分社会凝聚力和任务凝聚力,但与普通工作团队相反,社会凝聚力与主观和客观绩效均显著相关,而任务凝聚力仅对主观绩效有着显著影响。陈璐等(2012)针对中国家长式领导的研究发现,团队凝聚力与威权领导负相关,并中介威权领导的作用,使其与团队有效性负相关,这说明威权领导不利于激发高凝聚型高管团队的有效性,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风格更加适合于高凝聚型的中国家族企业管理。
(二)高管团队社会整合与行为整合
与普通工作团队不同,高层管理团队的行为很难被外界全面获知,为了增强对团队过程“黑箱”的了解,高管团队领域开始用社会整合和之后拓展的行为整合来探究过程特征。团队社会整合来自于Shaw(1981)的凝聚力构念(Carmeli和Schaubroeck,2006;O’Reilly等,1989),O’Reilly等(1989)将其定义为“群体的吸引力、对其他群体成员的满意度以及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互动”,并将团队成员间的心理和情感吸引力与有效决策相联系。本质上社会整合是指个体与团队其他成员心理上相连结的程度(Hambrick,1994),社会整合既包括感知到的和谐关系也包括成员吸引所产生的情感成分即团队凝聚力(Carmeli和Schaubroeck,2006;Guillaume等,2012)。Smith等(1994)发现,高管团队人口学背景、社会整合与沟通等群体过程直接影响组织绩效,人口学背景变量也通过群体过程间接影响组织绩效。然而,社会整合仅仅考察了高管团队中的社会维度,而对团队任务关注不够。其次,社会整合并不一定与良好的团队决策相联系,Janis(1972)认为,高凝聚力群体以维持和谐关系取代其任务属性,很难成功检验问题背后的假设并寻找其他替代方案,因而更容易导致较差的决策,即呈现群体迷思(groupthink)。
为此,Hambrick(1994)重新构造了包含特定社会和任务过程的行为整合概念。行为整合包括一个社会维度(高管团队的协作水平)和两个任务维度(团队质量和信息交换质量,以及对联合决策的倚重程度)。Hambrick(1994)认为,同时考察这些相互增强的过程因素较之单一维度更能获得高管团队的整体性和努力程度的完整性。行为整合与社会整合中的凝聚力这一核心情感维度相互联系,但在概念和操作化上存在一定差异(Simsek等,2005)。行为整合包含了全部高管团队的重要过程,既有社会和情感倾向(即社会整合),也包含了任务和行为趋势。行为整合较高的高管团队内部具有高质量的互动,有助于战略决策所需的信息获取、处理和解读能力的提升,因而产生了高质量的战略选择和组织结果(Bromiley和Rau,2016;Carmeli和Schaubroeck,2006)。这种多维度元构念在预测高管团队层面的复杂行为及绩效联系时,具有更好的预测效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Bromiley和Rau,2016;Ou等,2014)。
Simsek等(2005)在行为整合构念的基础之上,从CEO(集体主义导向、CEO任期)、高管团队(多元化、任期、规模)、公司(绩效、规模、年龄)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行为整合的形成因素,并在Mooney(2000)行为整合量表基础上开发出了九题项量表,分别测量协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维度。通过402家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尽管CEO、高管团队、公司每个层面的决定因素一定程度上都解释了行为整合的不同,但同时考察三个层面时解释的变异最多。Simsek等人(2005)的量表由于简便易行,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行为整合的主流度量方法(Bromiley和Rau,2016;Carmeli等,2011;Ou等,2014)。
Ensley等(2003)利用行为整合理论构造了新创企业的高管团队过程,并以此解释对新创企业的绩效影响。Carmeli和Schaubroeck(2006)对116家以色列公司的研究表明,行为整合较高的高管团队具有较高的战略决策质量,行为整合直接或者通过感知到的战略决策质量间接与组织衰退负相关。Carmeli(2008)进一步发现,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经济绩效和人力资源绩效显著正相关。深陷组织衰退中的高管团队面临着急剧且难以预料的变革,行为整合的绩效影响更为关键。Ling等(2008)发现,变革型CEO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冒险倾向、责任分权以及长期薪酬,这些高管团队特征进而影响公司创业精神。而CEO授权型领导风格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正相关,通过后者的中介增强了团队潜能和公司绩效(Carmeli等,2011)。Ou等(2014)进一步发现,正是CEO的谦逊行为引起了授权型领导力,并与团队行为整合正相关,由此使得中层管理者感知到了授权文化,从而引起一系列良好的组织结果如工作敬业度、情感承诺和工作绩效的提升。行为整合很好地解释了谦逊、授权型领导力与高管团队效能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这种中介效应可能在更广范围的诸如CEO或董事长特征与高管团队对接关系中也会存在,需要在未来研究中继续加以挖掘(Bromiley和Rau,2016)。
现有实证研究表明,较之单独的社会整合或者群体凝聚力,多维行为整合概念更加适合于高管团队层面的研究,对于战略决策以及组织结果等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行为整合理论在未来的高管团队甚至其他群体过程研究过程中具有较为广阔的研究潜力。行为整合也开始取代团队异质性成为高管团队研究的热点,国内外许多硕、博士学位论文也以行为整合作为选题。可以预料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深化,成为“微观基础运动”在高管团队领域最为重要的突破之一(Felin等,2015;Powell和Rerup,2016)。然而行为整合元构念囊括了信息交换、协作行为、共同决策质量等,涵盖了大部分高管团队互动过程和团队效能整体性指标,过分依赖于行为整合的中介机制可能掩盖了更加具体和具有实践意义的团队过程,尽管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很高但却很难指导管理实践,形成新的高管团队“过程黑箱”。
(三)高管团队冲突
团队冲突也是高管团队过程研究中关注较多的领域,冲突一般分为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陈建勋等,2016)。认知冲突是功能性的,指“任务导向且集中于如何更好实现共同目标的判断差异”(Amason,1996),因而也称为任务冲突、观念冲突等。高管团队成员通过不同观点考察战略方案时会产生认知冲突。尽管两种冲突在高管团队研究中也存在不一致或者不显著的情况,但通常认为任务导向的意见差异可以加深理解、提高整体决策质量,认知冲突因而被认为是有效战略决策必要和有益的组成。认知冲突故而与较好的组织绩效相联系,这在高管团队与非高管团队的对比中更为显著(de Wit等,2012)。情感冲突则是个人导向的意见不合,集中表现为人际厌恶和叛离,也被称为关系冲突、人际冲突等。正是情感维度的冲突导致了决策困难,情感冲突不仅降低了决策质量和理解,也降低了满意度和团队成员影响力,后者进而削弱了团队的未来有效性,情感冲突一般会阻碍绩效提升(de Wit等,2012;陈建勋等,2016)。
因此高效团队经常是鼓励认知冲突而抑制情感冲突,但是Ensley等(2002)发现,认知冲突与情感冲突正相关,说明认知冲突点燃和产生了人际间不满与不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凝聚力的归属维度阻碍这种关系从而起到了平衡两类冲突的作用。Simons和Peterson(2000)也发现了类似的调节机制,团队信任调节任务冲突与关系冲突间联系;尽管显著性较弱,但挑衅性冲突管理技巧使得任务与关系冲突的联系增强,可见团队内信任和管理技巧对于应对冲突极为重要。Li和Hambrick(2005)提出了派系群体概念,即群体成员代表着少数(通常为两个)社会实体,如重组整合团队、双边任务团队以及合资企业团队。针对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团队研究发现,派系间较大的人口学断层引起了任务与情感冲突,但只有情感冲突引发团队行为瓦解导致较差的绩效。他们关于任务冲突的假设与主流研究相悖,认为任务冲突也会导致行为解体进而降低决策有效性,这与他们所考察的特殊派系群体有关,这类群体中群内信任程度通常较低。任务与情感冲突的不同作用除了与信任、团队工作属性有关外,不同的情境因素如CEO领导风格也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如有研究发现CEO交易型或变革型领导力水平调节团队冲突与探索式学习行为之间的联系(陈建勋等,2016)。
五、狭义高管团队动力:战略决策过程研究企业中高管团队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有目共睹,深入理解群体互动或者群体动力对于战略决策的影响显得至关重要(Forsyth,2013)。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困难尤其是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等问题,基于战略决策过程的高管团队动力学研究相对于团队异质性、冲突、行为整合等显得较为匮乏(Finkelstein等,2008;Peterson等,2003)。但一些新的方法开始出现,案例研究等质性方法以及Peterson等(2003)基于定性和定量结合的Q方法等,为深入高管团队动力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一)基于GDQ的高管团队动力研究
无论高层管理团队还是一般的工作团队决策过程研究中,通常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假定良好的决策过程会获得“正确”的决策选择,进而导致好的团队或者组织结果(Janis和Mann,1977;Zey,1992)。Janis和Mann(1977)的七步决策模型是理性选择理论比较典型的例子,认为良好的过程应该尽可能寻找所有的决策方案、调查所有目标和每个决策选择的价值所在、成本及风险的全面评估、重新搜集信息并吸纳专家判断进行所有替代方案再评估等。截至目前,理性选择模型仍然是团队过程及决策研究的主流,高管团队研究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理性选择模型的固有缺陷,如过度理性、效用最大化、效用主观化,忽视了政治、价值观、情感以及文化的作用等,因此也备受挑战(Zey,1992)。
Peterson等人在此基础上,运用较为创新的Q方法①对企业高管团队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数据来源或者直接接触高管团队成员非常困难时,Q方法为非介入式研究团队过程等提供了极大便利(Peterson等,2003;Wong等,2011)。Peterson等(1998)首次将政治群体动力Q-sort量表(group dynamic Q-sort,GDQ)修订为公司型GDQ来评估公司中TMT团队动力。他们开发了8个群体过程指示量表,并确定了7种理想的理论决策模型(ideal type)(Peterson等,1998),后来又将理想理论模型拓展到10个(Peterson等,1999b;Peterson等,2003)。公司型GDQ的8个群体过程指标与政治群体动力Q-sort量表基本类似,包括智力僵化—灵活性、危机—控制程度、乐观—悲观、领导者的劣势—优势、派系主义—凝聚性、守法—腐化性、分权—集权程度、风险规避—冒险。
① Q方法(Q methodology)又称Q分类法、Q排序技术(Q-sort),是统计学家William 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用于评估人类主观性的一种统计方法,通常要求个体对表述不同观点的大量题项(称为Q sample)进行强制性排序以便量化排序从而获得个体侧写(personal profiles),之后将个体侧写与他人侧写或者理论模型(ideal type)进行相关分析等。Q方法与普遍采用的对一大群人进行客观测量的问卷调查并进行相关分析的R方法不同,Q方法以人(person)为中心,而R方法则是以变量(variables)为中心的研究。
Peterson等(1998)在Janis(1972)的“群体迷思团队”、“机警决策团队”的基础上,根据组织行为理论关于高管团队成败分析的五个重要文献重新构建了五类理想团队,包括来自于资源依赖观的“有效决策”团队、“企业社会责任”团队、“全盛组织”团队、“下滑组织”团队、“专制主义式个人崇拜(absolutist cult)”团队等。Peterson等(1999a)又根据组织理论中的X理论和Y理论、Z理论等提出了X理论团队、Y理论团队、Z理论团队。十种理想团队模型囊括了主流理论中最为经典的积极与消极团队类型,实际高管团队进行评估后即可与其进行比对,从而了解实际团队的运作模式。
针对美国7家“财富500强”公司的13个CEO及其高管团队,按照成功与不成功相对应分类后进行的团队动力研究表明,团队决策过程与团队结果系统性相关(Peterson等,1998)。但团队成功与否并不能单纯依赖于过程质量来判断,成功的团队也会存在团队迷思,而失败型团队也有机警的特征。这种团队动力与历史案例相结合的研究,可以拓展高管团队甚至其他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Peterson等(1999,2003)又将研究扩大到9家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17个CEO及高管团队之中。其中,Peterson等(1999a)较深入地检验了群体过程指标与组织绩效在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关系,发现不同的群体过程与三个绩效间的相关性并不一致,说明团队特征的组织影响在企业演化的过程中作用并不相同。团队的开放性、智力灵活性、集权与过去两年的绩效显著正相关;团队凝聚力、乐观、冒险与当期绩效正相关;团队冒险倾向则与未来绩效正相关。Peterson等(2003)进一步检验了CEO大五人格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发现高管团队动力中介了CEO人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不同的CEO人格维度也与高管团队动力特征的不同侧面相联系;乐观、智力灵活、高凝聚力的分权型团队收入增长明显,但高冒险团队也会促进收入增长,可见冒险精神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Wong等(2011)采取了Q方法以及Peterson等(1998)开发的群体动力量表,对1996—2002年的61家财富500强企业的高管团队决策过程进行了大样本的质性数据搜集和团队过程Q方法排序。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决策过程中,能够区分和综合不同观点的复杂性整合能力与团队分权与公司社会绩效正相关,决策分权进而调节复杂性整合能力与绩效间关系,分权程度越高则复杂性整合能力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绩效。可见高管团队不同的群体动力维度可能相互影响或者成为重要的中介与调解机制影响组织结果。
总之,Peterson等人的研究利用全新的方法对Janis(1972)的群体迷思理论等通过著名的商业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究,Janis关于群体过程与决策质量以及绩效相关的结论基本得到支持,但具体表现有所差异。首先,团队群体迷思和机警决策都可能导致决策成功或失败,这可能与群体的发展阶段以及规模有关。其次,这些研究将CEO人格与群体动力的过程指标相联系,证实多种领导者人格影响高管团队决策过程。第三,GDQ过程研究方法解决了以往对历史案例无法进行严谨的定量分析或者数据获取极端困难时无法开展战略决策过程研究的难题(Peterson等,2006;Wong等,2011)。
(二)基于质性方法的高管团队研究
除了基于GDQ的高管团队动力研究,案例以及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尤其适合这一领域(Barr,2004;Hitt等,2007);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也可以提高高管团队研究的“有用性”(Priem等,1999)。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是早期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高管团队过程研究的范例,基于高速变动环境中的8家计算机企业的案例,他们对公司政治如何影响高管战略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高管影响决策的公司政治行为来自于权力集中。专权的CEO在公司内部“经营”并在下属中引发政治行为,进而通过年龄等人口学背景特征形成稳定的主导联盟,但高管团队政治活动负向影响企业绩效。这一研究揭开了高管团队政治行为的神秘面纱,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真正”触及了高管团队内部的运作过程,所建构的理论有趣并极具实践意义。
不同层级的领导力意义建构在公司内部具有重要的影响,但量化实证研究很难考察它们的成因及影响。Raes等(2007)另辟蹊径,通过23个高管团队的会议记录深入考察了高管团队对中层管理者的领导力意义建构过程。研究发现,领导力意义建构包含了中层与高层的形象特征并反映到行动及计划之中,并成为了高管团队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层管理者的领导力意义建构以及领导行为是解释高管团队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过程。对于创业企业中的隐形知识传播以及技术与商业知识的作用,Knockaert等(2011)发现,研发团队成员大量加入创业团队时更有利于高科技隐性知识的传播,但只有当研发与负责商业化的成员认知差异较小时,团队中专门性商业知识和技能的作用才比较明显。混合研究方法在Kwee等(2011)中得到了充分利用,对荷兰皇家壳牌1907—2004年将近百年的高管团队的公司治理倾向与战略更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公司治理倾向的高管团队更容易追求开发式(exploitative)和外部增长型战略更新,而具有德法等欧洲大陆遵循的莱茵河模式公司治理倾向的高管团队则会追求探索式(exploration)和内部增长型战略更新。从公司的历史演化来看,这一研究也是对高管团队过程的一种整体性探究,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创新性。
部分国内学者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情境中独特的高管团队现象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张仁江和田莉(2013)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对高管团队特征演化进行了长达8年的现场观察和跟踪,发现在层级结构组织内,派系冲突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冲突双方势均力敌以及一方认为对方触动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冲突演化的路径是从认知冲突到情感冲突,最终转化为派系冲突。认知和情感阶段冲突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升级为派系冲突后则会明显降低企业绩效。罗瑾琏等(2014)也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针对高管调入探究了领导行为对管理团队知识转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愿景式”调动高管的愿景激励对知识转移影响有限,但组织文化建设尤其是分权式的管理明显促进了团队内部知识转移;“家长式”调动高管的威权领导行为能有效管理处于困境中的管理团队,仁慈领导行为和德行领导行为均有助于知识转移;“公仆型”调动高管以身作则的领导行为和利他主义理念也为管理团队知识转移提供了有力支持。周键(2016)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了创业团队协作和创业管理强度促进创业企业成长的两种演化路径和机制,即个体推动型和团队推动型。两种演化路径的推动力不同,过程也不尽相同,但结果却殊途同归,都会增强创业团队协作与管理强度提升。该研究表明不存在最优的创业发展路径,创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业特点与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路径,团队氛围浓厚的创业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创业团队的作用,以团队带动创业员工;创业者掌握较多资源的企业则应充分发挥创业者的能动性,进而通过创业团队协作和管理强度推进创业进程。
国内外纵向案例研究尽管为数不多,但都深入到高管团队内部,对量化研究难以触及的领导力意义建构、创业团队知识的作用、公司治理风格与企业战略更新、派系冲突演化、高管调动引发的知识转移以及创业团队演化与创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弥补了量化研究在“深层”团队互动以及团队过程和历史演化方面的不足(Klenke,2016)。与主流的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提供了全景式的“真实”团队动力机制,研究结果不仅弥补了高管团队动力以及相关领域的理论不足,许多发现也可为管理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尽管国内质性研究更为稀少也很少出现在顶级期刊,但可喜的是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质性研究对于中国情境的重要性并展开了积极探索,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于高管团队过程复杂性以及演化特征的了解。
六、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方向(一)中国情境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近年来高阶梯队理论应对学术界的批判,开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由单一的CEO或者董事长等个人特征研究向高管团队研究转变,并寻求更加贴近战略决策过程的背景变量来增强研究的解释力(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与此相适应,高管团队研究在中国也成为了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并将高管团队研究与特定的背景变量结合,对各类战略选择及组织绩效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检验。国内高管团队研究大多集中于广义团队动力范畴的团队结构、团队构成以及冲突、凝聚力等方面,团队构成方面注意到了垂直对等关系的独特性,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贺远琼等,2009)。
国内高管团队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不足。
第一,从高阶梯队理论的过程模型来看,国内研究大多仍然集中在高管团队的构成与结构等“浅层”人口学背景变量方面,而对影响团队过程的“深层”背景或者决策过程的关注较少,仅有零星的案例研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第二,高管团队的人口学背景变量的选择较为单一,对于影响战略决策过程的“深层”特征挖掘较为缺乏,尤其是在关注较多的团队异质性研究中,忽视了团队异质性的多维性及多种度量方法(Bunderson和Sutcliffe,2002;Harrison和Klein,2007),导致研究结论的简单化或不一致。
第三,对于影响高管团队运作的中国特定情境的挖掘大多停留在所有权、股权集中度、董事长或者CEO权力等容易度量的个别因素之中,而对政府管制、官员背景高管、差序格局与强关系、组织文化以及当前快速发展的家族企业、创业与创新、互联网等技术进步的影响则关注较少。
第四,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采取以量化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案例等质性研究或混合研究方法还处于零星的尝试之中,导致高管团队领域的理论建构或者创新观点较为缺乏。
(二)现有高管团队动力研究存在的问题
作为高阶梯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管团队动力研究已成为高管团队研究应对理论挑战的前沿领域,新的研究大量出现,加深了对高管团队“过程黑箱”的了解。然而高管团队动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尽管国内外相关研究中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第一,高管团队背景变量不够丰富,更多集中于传统的“浅层”人口学背景之中,导致背景变量所代理的潜在心理特征较为模糊或者因果链条较远,从而影响了研究的解释力(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应将更为广泛的高管背景、尤其是与高管团队过程和战略决策联系更为紧密的“深层”背景变量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尽可能直接度量心理特征或者采取非介入式多指标度量等。不仅要研究它们的直接效应,也要考察多种异质性甚至角色依赖导致的成对关系差异的组织影响,如教育的多样性、政治态度、越轨行为、任职背景中的内外部评价多样性、合法与灰色创业经历、互联网行业的任职背景以及多种心理特征的考察。
第二,对于情境因素的挖掘应该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将欧美高管团队研究应用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时,应该关注外部宏观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特定的公司治理特征、公司与国家文化、权力构成等的影响。由于正式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非正式关系的流行,应将组织与群体社会资本(Oh等,2006)等作为重要的情境或者团队构成要素纳入到发展中国家公司高管团队动力研究架构内。
第三,有关高管团队战略决策全过程的研究仍显不足,仅有的零星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对团队整体决策过程的了解较之以往更为深入,但高管团队的“过程黑箱”问题仍然存在,团队决策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很多量化研究中处于预设状态。
第四,研究方法单一,过度偏重于量化研究,影响了以上三方面的深入探究,在团队过程研究中尤为明显,影响了高管团队层面新现象的发掘和新的理论建构。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等质性方法、Q方法或者混合研究方法可以弥补当前量化研究的不足,为深入高管团队“过程黑箱”提供必要的帮助。在中国情境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等技术发展使得创业活动极为活跃,新创企业甚至早期的家族企业以及国有企业都面临着急剧变化,高管团队的一些演化议题如团队形成、更替、继任以及战略决策过程都可能与西方团队呈现较大差异,质性与混合研究方法更有助于挖掘这些新现象,并形成“中国特色”的高阶梯队理论创新。
(三)未来研究机会与建议
结合以上关于高管团队构成、结构以及团队过程的文献综述,本研究在图2中揭示了未来研究的机会点以及可能的突破(以图中黑色实心标志),通过广义团队动力框图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这些机会点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情境因素的关系。高管团队作为公司中最为重要的决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特征反映在公司的行为与结果中,然而这种反映更多地来自于高管团队深层的心理特征以及互动过程,而非浅层的人口学背景变量,因此高管团队动力研究的机会主要在于更加贴近深层特征,并通过动态过程来揭示他们对于公司行为和结果的影响(Finkelstein等,2008)。
首先,从过程模型的整体来看,当前关于高管团队构成、结构、团队过程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仍不够深入,要么聚焦于有限维度要么忽视了其他因素的情境或者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关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将高管团队以及整合互动过程视作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随着新的团队变量以及团队异质性度量的出现,不同的高管团队构成如何调节其对于战略选择或组织绩效的影响,团队过程中的行为整合、凝聚力、冲突如何影响团队构成与结构,这些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其次,高阶梯队理论所预示的高管个人或者团队特征对于组织行为和结果的影响与其工作任务和作用情境密切相关。工作任务差异除了高管团队内部职能不同外(Menz,2012),也与不同的战略选择任务或工作属性有关,比如海外并购或者新产品研发等可能给高管团队带来更高的任务要求(Hambrick等,2005),不同的工作需求背景下高管团队的构成、结构以及团队过程对战略选择和组织结果的影响并不相同。因此在战略选择中应该更多关注研发、创业以及高管团队成员的解职、更替以及继任等目前关注较少的领域,某种比较稳定的团队构成或结构可能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绩效,而是为了确保继任计划的完成或者渡过难关。我国第一代家族企业创业者大多面临着交接班等家族控制权的转让难题,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可供选择的继任候选人极为有限,“传男”或“传女”还是交由其他家族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都是中国情境下重要的战略选择议题。
在组织内部情境因素中,创业演化、家族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情境对于高管团队动力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家族与国有企业除了追求经济绩效之外,更为重要的社会情感财富也会介入其中(Chua等,2015;汪金爱等,2012)。而外部环境因素除了关注转型经济等带来的制度影响之外,当前的经济波动以及技术冲击对于高管团队的影响,经济萧条背景下团队的构成、结果与过程如何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带来的虚拟化(如虚拟组织、网络互动等)是否会影响高管团队等议题也值得关注。
再次,随着相互依赖性概念的引入,高管团队结构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Hambrick等,2015),团队结构中的垂直组对、派系、差序格局、CEO-TMT与董事长-TMT对接(Bromiley和Rau,2016;Raes等,2011)甚至特殊股东如控制家族与国有企业中的团队结构亟待深入挖掘。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有可能解释中国情境中独特的组织现象并丰富高管团队理论。另外,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组织情境如何影响高管团队构成和结构也值得关注,如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许多高管团队吸纳了急需的国外专业人才,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中国政府官员创业或者加入高管团队,“反腐”运动带来的高管团队构成变化及影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最后,团队过程研究中行为整合概念的强大解释力引起了国外多个研究领域的关注,国内研究也应继续跟进,并对中国独特的高管团队现象进行研究,如国有企业、家族企业、创业企业团队中的影响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企业的高管团队也在体验着国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要经历的发展历程,独特的制度及文化背景使得中国情境下的高管团队互动过程更为复杂,案例、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以及混合研究方法等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可以深入到高管团队“过程黑箱”内部,打开更为有趣的理论建构空间,并增强研究的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关系。
| [1] | 白云涛, 郭菊娥, 席酉民. 高层管理团队风险偏好异质性对战略投资决策影响效应的实验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7(2): 25–30. |
| [2] | 陈建勋, 郑雪强, 王涛. " 对事不对人” 抑或 " 对人不对事”——高管团队冲突对组织探索式学习行为的影响[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5): 91–103. |
| [3] | 陈璐, 杨百寅, 井润田. 家长式领导对高管团队有效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团队凝聚力为中介变量[J]. 管理工程学报, 2012(1): 13–19, 34. |
| [4] | 何威风, 刘启亮.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7): 144–155. |
| [5] | 贺远琼, 杨文, 陈昀. 基于Meta分析的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 软科学, 2009(1): 12–16. |
| [6] | 胡望斌, 张玉利, 杨俊. 同质性还是异质性: 创业导向对技术创业团队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J]. 管理世界, 2014(6): 92–109, 187–188. |
| [7] | 姜定宇, 郑伯埙. 华人差序式领导的本质与影响历程[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14(42): 285–357. |
| [8] | 姜付秀, 朱冰, 唐凝. CEO和CFO任期交错是否可以降低盈余管理[J]. 管理世界, 2013(1): 158–167. |
| [9] | 蒋春燕. 高管团队要素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长三角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实证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3): 72–84. |
| [10] | 林浚清, 黄祖辉, 孙永祥. 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公司绩效和治理结构[J]. 经济研究, 2003(4): 31–40, 92. |
| [11] | 刘永丽. 管理者团队中垂直对特征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2): 107–116, 128. |
| [12] | 鲁倩, 贾良定. 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权力与企业多元化战略[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5): 181–187. |
| [13] | 罗瑾琏, 许方佩, 钟竞. 高管领导行为对管理团队知识转移影响的案例研究——基于民营集团内高管调动的视角[J]. 商业研究, 2014(5): 115–124. |
| [14] | 孟晓华, 曾赛星, 张振波. 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系统管理学报, 2012(6): 825–834. |
| [15] | 任颋, 王峥.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0(5): 81–91. |
| [16] | 孙海法, 姚振华, 严茂胜. 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对纺织和信息技术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J]. 南开管理评论, 2006(6): 61–67. |
| [17] | 汪金爱, 章凯, 赵三英. 为什么CEO解职如此罕见? 一种基于前景理论的解释[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1): 54–66. |
| [18] | 汪金爱, 宗芳宇. 国外高阶梯队理论研究新进展: 揭开人口学背景黑箱[J]. 管理学报, 2011(8): 1247–1255. |
| [19] | 王建斌. 差序格局下组织行为特征及其管理方式[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2): 58–62. |
| [20] | 王明琳, 徐萌娜, 王河森. 利他行为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吗?——基于家族企业中亲缘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3): 144–157. |
| [21] | 王重鸣, 刘学方. 高管团队内聚力对家族企业继承绩效影响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7(10): 84–98. |
| [22] | 肖挺, 刘华, 叶芃.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服务行业上市公司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3(8): 125–135. |
| [23] | 薛有志, 李国栋. 国际化战略实施与高层管理团队构成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09(11): 1478–1485. |
| [24] | 杨林.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所有制与创业战略导向——基于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9): 159–171. |
| [25] | 杨林. 创业型企业高管团队垂直对差异与创业战略导向: 产业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的调节效应[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1): 134–144. |
| [26] | 杨林, 杨倩. 高管团队结构差异性与企业并购关系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 2012(11): 57–57. |
| [27] | 杨志强, 王华. 公司内部薪酬差距、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行为——基于高管团队内和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的比较分析[J]. 会计研究, 2014(6): 57–65. |
| [28] | 姚冰湜, 马琳, 王雪莉. 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CEO权力的调节作用[J]. 中国软科学, 2015(2): 117–126. |
| [29] | 曾萍, 邬绮虹.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回顾与展望[J]. 经济管理, 2012(1): 190–199. |
| [30] | 张龙, 刘洪. 高管团队中垂直对人口特征差异对高管离职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09(4): 108–118. |
| [31] | 张仁江, 田莉. 高管团队派系冲突的诱发前提、演化机理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基于HB公司的纵向跟踪研究[J]. 财贸研究, 2013(1): 123–130, 139. |
| [32] | 周键. 团队协作、管理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一个跨案例研究[J]. 经济管理, 2016(2): 47–56. |
| [33] | Amason A C. Distinguishing the effects of functional and dysfunctional conflict 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Resolving a paradox for top management tea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1): 123–148. |
| [34] | Barr P S. Current and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qualitative methods in strategy research[J].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2004, 1(1): 165–188. |
| [35] | Barrick M R, Bradley B H, Kristof-Brown A 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interdep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real teams and working group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3): 544–557. |
| [36] | Beal D J, Cohen R R, Burke M J. Cohesion and performance in groups: A Meta-analytic clarification of construct relation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6): 989–1004. |
| [37] | Bromiley P, Rau D. Social,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influences on upper echelons during strategy process: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42(1): 174–202. |
| [38] | Bunderson J S, Sutcliffe K M. Comparing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s of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management teams: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effec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5): 875–893. |
| [39] | Carmeli A. Top management team behavioral integr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 organizations[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08, 33(6): 712–735. |
| [40] | Carmeli A, Schaubroeck J. Top management team behavioral integration, decision qu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declin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6, 17(5): 441–453. |
| [41] | Carmeli A, Schaubroeck J, Tishler A. How CEO empowering leadership shapes top management team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firm performanc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1, 22(2): 399–411. |
| [42] | Carpenter M A. Th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y and social context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and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3): 275–284. |
| [43] | Chatman J A, Flynn F J.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heterogeneity on the emerg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cooperative norms in work tea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5): 956–974. |
| [44] | Chua J H, Chrisman J J, De Massis A. A closer look at socioemotional wealth: Its flows, stocks, and prospects for moving forward[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2): 173–182. |
| [45] | Cohen S G, Bailey D E. What makes teams work: group effectiveness research from the shop floor to the executive suit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7, 23(3): 239–290. |
| [46] | De Wit F R, Greer L L, Jehn K A. The paradox of intragroup conflict: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97(2): 360–390. |
| [47] | Eisenhardt K M, Bourgeois L J. Politics of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in high-velocity environments: Toward a midrange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31(4): 737–770. |
| [48] | Eisenhardt K M, Schoonhoven C B. Organizational growth: Linking founding team, strategy, environment, and growth among US semiconductor ventures, 1978-1988[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3): 504–529. |
| [49] | Ensley M D, Pearson A, Pearce C L. Top management team process, shared leadership,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3, 13(2): 329–346. |
| [50] | Ensley M D, Pearson A W. An exploratory comparison of the behavioral dynamics of top management teams in family and nonfamily new ventures: Cohesion, conflict, potency, and consensu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29(3): 267–284. |
| [51] | Ensley M D, Pearson A W, Amason A C.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new venture top management teams: Cohesion, conflict,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2, 17(4): 365–386. |
| [52] | Felin T, Foss N J, Ployhart R E. The microfoundations movement i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theo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5, 9(1): 575–632. |
| [53] | Finkelstein S, Hambrick D C, Cannella A A. Strategic leadership: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xecutives, top management teams, and board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8. |
| [54] | Forsyth D R. Group dynamics[M].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3. |
| [55] | Guillaume Y R, Brodbeck F C, Riketta M. Surface‐and deep-level dissimilarity effects 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dividual effectiveness related outcomes in work groups: A meta‐analytic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2, 85(1): 80–115. |
| [56] | Hambrick D C. Top management groups: A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he " team” label[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4a, 16(2): 171–214. |
| [57] | Hambrick D C, Finkelstein S, Mooney A C. Executive job demands: New insights for explaining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leader behavio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3): 472–491. |
| [58] | Hambrick D C, Humphrey S E, Gupta A. 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 within top management teams: A key moderator of upper echelons predic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3): 449–461. |
| [59] |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
| [60] | Harrison D A, Klein K J. What’s the difference? diversity constructs as separation, variety, or disparity i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4): 1199–1228. |
| [61] | Hitt M A, Beamish P W, Jackson S E. Buil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ridges across levels: Multilevel research in manage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6): 1385–1399. |
| [62] | Homberg F, Bui H T.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 A systematic review[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3, 38(4): 455–479. |
| [63] | Horwitz S K, Horwitz I B. The effects of team diversity on team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eam demograph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33(6): 987–1015. |
| [64] | Janis I L. Victims of groupthink: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2. |
| [65] | Janis I L, Mann L.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M].New York:Free Press, 1977. |
| [66] | Kearney E, Gebert D, Voelpel S C. When and how diversity benefits teams: The importance of team members’ need for cogni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3): 581–598. |
| [67] | Klenke K.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leadership[M].Bingle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6. |
| [68] | Knockaert M, Ucbasaran D, Wright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er, top management team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science‐based entrepreneurial firm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35(4): 777–803. |
| [69] | Kwee Z, Van Den Bosch F A, Volberda H W.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s corporate governance orientation on strategic renewal trajectori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Royal Dutch Shell Plc, 1907-2004[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5): 984–1014. |
| [70] | Li J T, Hambrick D C. Factional groups: A new vantage o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conflict, and disintegration in work tea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5): 794–813. |
| [71] | Ling Y, Simsek Z, Lubatkin M H.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s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Examining the CEO-TMT interfa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51(3): 557–576. |
| [72] | Mathieu J, Maynard M T, Rapp T. Team effectiveness 1997-2007: A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ments and a glimpse into the fu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34(3): 410–476. |
| [73] | Mathieu J E, Tannenbaum J E, Donsbach J S.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of team composition models: Moving toward a dynamic and tempor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40(1): 130–160. |
| [74] | Menz M. Functional top management team members: A review, synthesis,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38(1): 45–80. |
| [75] | Michalisin M D, Karau S J, Tangpong C. The effects of performance and team cohesion on attribution: A longitudinal simul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4, 57(10): 1108–1115. |
| [76] | Mooney A C. The Antecedents to conflict during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The importance of behavioral integration[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2000. |
| [77] | Mullen B, Copper C. The relation between group cohesiveness and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on[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115(2): 210–227. |
| [78] | Nielsen B B, Nielsen S. Top management team nationality divers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A multilevel stud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3): 373–382. |
| [79] | Nielsen S.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0, 12(3): 301–316. |
| [80] | O’reilly C A, Caldwell D F, Barnett W P. Work group demograph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urnove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9, 34(1): 21–37. |
| [81] | Oh H, Labianca G, Chung M-H. A multilevel model of group social capita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3): 569–582. |
| [82] | Ou A Y, Tsui A S, Kinicki A J. Humbl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connections to top management team integration and middle managers’ respons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4, 59(1): 34–72. |
| [83] | Peterson R S, Owens P D, Martorana P V. The group dynamics q-sort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new method for studying familiar problem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999b, 2(2): 107–139. |
| [84] | Peterson R S, Owens P D, Tetlock P E. Group dynamics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Groupthink, vigilance, and alternative models of organizational failure and succes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8, 73(2-3): 272–305. |
| [85] | Peterson R S, Smith D B, Martorana P V. Choosing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when data are scarce and the questions important: Reply to Hollenbeck, Derue, and Mannor (2006)[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6, 91(1): 6–8. |
| [86] | Peterson R S, Smith D B, Martorana P V. The impact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personality on top management team dynamics: One mechanism by which leadership affects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795–808. |
| [87] | Powell W W, Rerup C. Opening the Black Box: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s[A]. Greenwood R, Oliver C, Suddaby R, et al.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C].2nd ed. [S.l.]: Sage Publishers, 2016. |
| [88] | Priem R L, Lyon D W, Dess G G.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demographic proxies in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9, 25(6): 935–953. |
| [89] | Quigley T J, Hambrick D C. Has the " CEO effect” increased in recent deca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great rise in america’s attention to corporate leader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6): 821–830. |
| [90] | Raes A M, Glunk R U, Heijltjes M G.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middle managers making sense of leadership[J]. Small Group Research, 2007, 38(3): 360–386. |
| [91] | Raes A M, Heijltjes M G, Glunk U. The interface of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middle managers: A process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1): 102–126. |
| [92] | Sanders W G, Carpenter M A.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rm governance: The roles of CEO compensation, top team composition, and board struc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2): 158–178. |
| [93] | Shaw M. Group dynamics: The psychology of small group behavior[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 [94] | Simons T L, Peterson R S. Task conflict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The pivotal role of intragroup trus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0, 85(1): 102–111. |
| [95] | Simsek Z, Veiga J F, Lubatkin M H. Modeling the multilevel determinant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behavioral integr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1): 69–84. |
| [96] | Smith K G, Smith K A, Olian J D. Top management team demography and process: the ro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4, 39(3): 412–438. |
| [97] | Talke K, Salomo S, Kock A.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orientation: The relationship and consequences for innovativeness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1, 28(6): 819–832. |
| [98] | Wong E M, Ormiston M E, Tetlock P E. The effect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integrative complexity and de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6): 1207–1228. |
| [99] | Zey M. Criticisms of rational choice models[A]. Zey M.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 A Critique[M].Newbury Park, CA: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2. |
 2017, Vol. 39
2017, Vol.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