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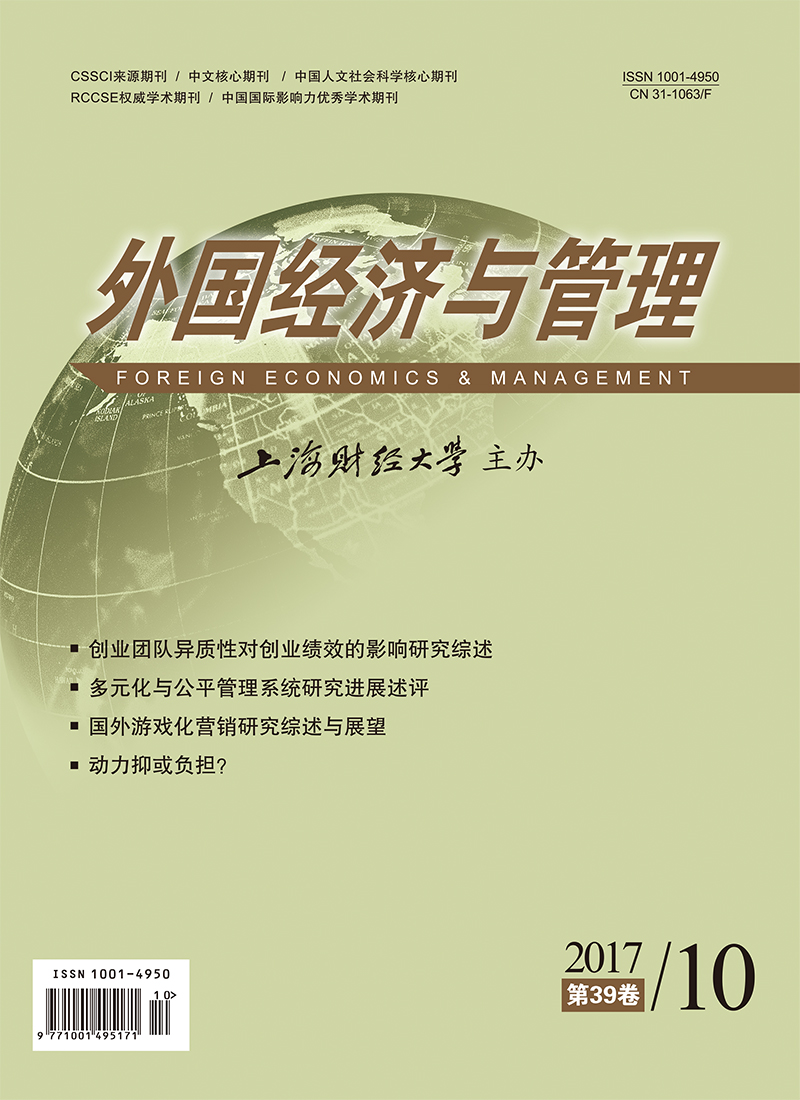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年39卷第10期 |
- 张燕, 李贵卿
- Zhang Yan, Li Guiqing
- “肮脏”工作:概念、测量以及对从业者的影响
- Dirty work: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n dirty work practitioners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10): 86-101
-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7, 39(10): 86-101.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7-0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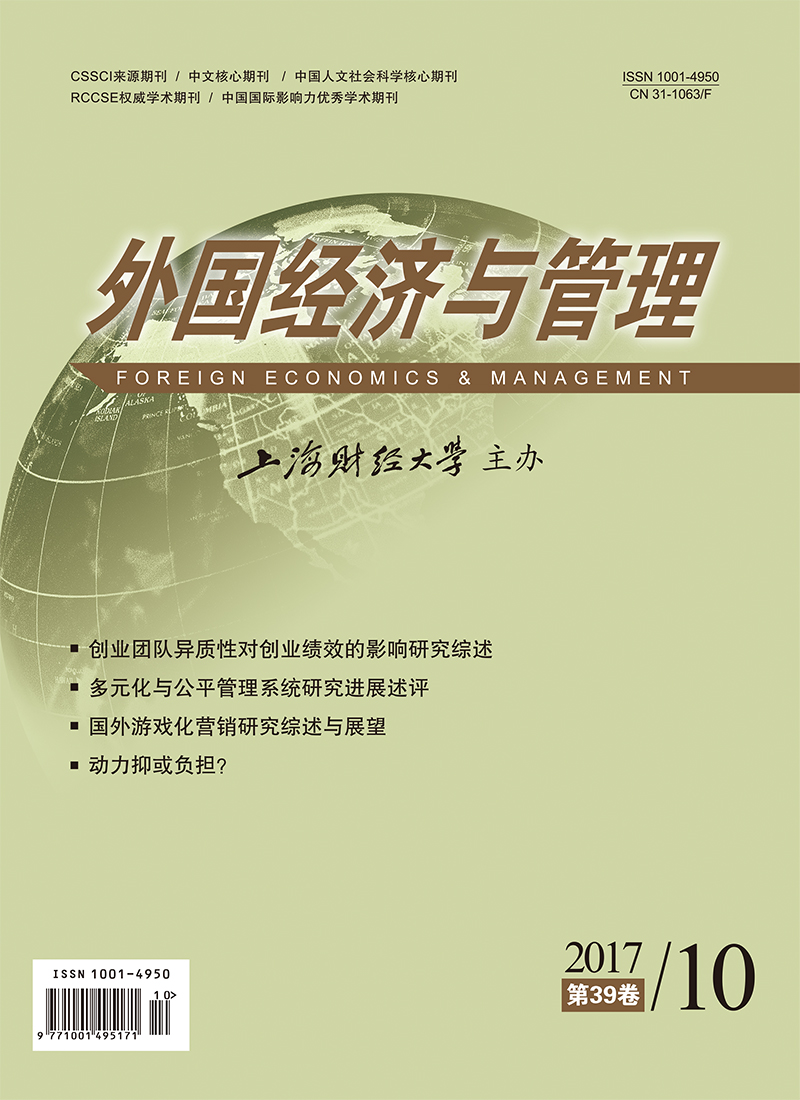
2017第39卷第10期
2.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3
2.School of Management,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610103, China
“肮脏”工作(dirty work)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为社会所贬低、鄙视和不喜欢的工作。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Hughes首次提出“肮脏”工作这一概念,直到2005年美国真人秀节目《Dirty Jobs》的热播引起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肮脏”工作研究才得到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Simpson等,2012)。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肮脏”工作在劳动力市场都一直被边缘化,存在严重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肮脏”工作的特性也给企业相关职位的招聘、留用、激励和职业安全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困难。但管理学理论界较少从职业的“肮脏”污名视角来分析这类工作的“用工难”和高流动率问题。现有研究表明,“肮脏”工作污名不仅给从业者带来自我认同危机和巨大压力,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身心健康问题,而且还是导致组织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Ashforth和Kreiner,1999)。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肮脏”工作的概念与分类、“肮脏”工作的测量以及“肮脏”工作对其从业者的影响等方面对国内外有关“肮脏”工作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对“肮脏”工作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推动有关“肮脏”工作的研究进展。
二、“肮脏”工作的概念(一)“肮脏”工作的定义
“肮脏”(dirty)一词,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中都包含两层意思:(1)不干净,不卫生;(2)丑恶,见不得人。从字面意思来看,“肮脏”除了指物质实体的不洁,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因此,Hughes用“肮脏”工作这一术语来表示那些具有令人反感的、令人厌恶的、危险的、地位低下的、不道德的、令人鄙视的等特征的工作。他认为“肮脏”工作是满足社会功能所需的工作或任务,但却遭遇社会的边缘化,导致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承受着污名(sigma)(Hughes,1971)。Emerson和Pollner(1976)强调“肮脏”工作是“被社会认定为肮脏的工作”,他们将“肮脏”工作定义为“为从业者带来压力和紧张感的、令人厌恶的、令人羞耻的或地位受到贬损的工作或任务”。他们强调“肮脏”是社会所建构的,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知。“肮脏”并不存在于工作本身,也不存在于从业者的个人特质中,而是社会和个人的感知(Simpson等,2012)。Ashforth和Kreiner(1999)沿用Hughes(1971)的定义,将“肮脏”工作定义为社会必要的,但是令人不愉快的、有损身份的或受到社会质疑的工作。他们认为工作被视为“肮脏”是基于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工作涉及有形的身体肮脏;工作象征着个人的堕落或自我尊严的丧失;工作以某种方式与社会大众的道德观背道而驰。Ashforth和Kreiner(1999)认为“肮脏”工作会激起人们不喜欢和厌恶的反应是因为违反了社会的“正常或洁净”工作的标准。公众会给这类工作贴上负面标签,从而产生偏见、歧视等,进而导致这类工作被污名化(stigmatized)。因此,“肮脏”工作与职业的污名化密不可分,甚至很多研究将“肮脏”工作也称为污名化工作(stigmatized occupation、tainted occupation、stained occupation)。Kreiner等人(2006)将“肮脏”工作定义为“在某一社会背景下被视为不洁的、令人反感的或丢脸的工作任务”,他们认为所有的职业都涉及“肮脏”,只是在“肮脏”的程度上存在差异。
整体而言,后续学者基本上都沿用了Hughes(1971)以及Ashforth和Kreiner(1999)对“肮脏”工作的定义,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共识。简言之,“肮脏”工作是指社会所必需的,在社会公众眼里是道德败坏的(道德肮脏)、有损身份的(社交肮脏),或不卫生或危险的(身体肮脏)令人厌恶的任务或职业,如保洁、家政、餐饮服务、护理、娱乐场所工作等(Ashforth等,2007)。
(二)“肮脏”工作的特征
1. “肮脏”工作的社会建构性
Mary Douglas在其著作《洁净与危险》中指出,事物是洁净还是肮脏,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是否符合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分类体系(Douglas,2002)。洁净与肮脏并非事物的本质,而是社会赋予的象征,决定事物在该体系中的分类。由此可知:(1)“肮脏”工作是一种社会区分。“肮脏”工作来自于人类的分类体系建构(Dick,2005;Tyler,2011)。“肮脏”工作的象征意义在于将“干净的我们”和“肮脏的他们”区分开来,便于人们将有价值的、可接受的、干净的、纯洁的、有序的、无瑕疵的“好”工作,与无价值的、不可接受的、被污染的、混沌的、有瑕疵的“坏”工作进行区分(阎书昌,2011)。(2)“肮脏”工作是一种污名。由于工作的“肮脏”属性违反了社会关于“正常或洁净”工作的标准,这种负面的社会标签使“肮脏”工作的从业者被社会认定为“偏差者”(deviant),导致他们拥有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Kraus,2010)。(3)“肮脏”工作是情境依赖和动态变化的。工作中的“肮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沿袭和地理位置中,“肮脏”有不同的解读,“肮脏”工作只是被社会和文化所定义的“不合适的事情”(Lai等,2013)。例如,护士在大多数国家被视为涉及身体“肮脏”但道德高尚的职业,然而Hadley等(2007)在孟加拉的研究发现,由于宗教和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女性从事护理职业被认为是道德“肮脏”的,因为她们要值夜班、与陌生人有身体接触。由此可见,由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一种情境下的“肮脏”工作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可能是中性的甚至正面的。因此,“肮脏”是可变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工作的“肮脏”特质既非不可避免,也非永久不变(Dick,2005;Tracy和Scott,2006)。
2. “肮脏”工作的任务/职业导向性
Ashforth和Kreiner(1999)在系统地归纳“肮脏”工作的定义时,将其描述为一种任务或职业。因此,“肮脏”工作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1)基于职业的“肮脏”工作研究。这是“肮脏”工作研究的主流,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关注“肮脏”特征突出的职业(如,监狱警务工作、护理工作、屠宰工作、精神病医务工作),探讨这些职业的“肮脏”污名对从业者职业认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Ashforth等,2007;Lopina等,2012;Bove和Pervan,2013;Worrall和Mawby,2013;Asher,2014;Shantz和Booth,2014;Makkawy和Scott,2017)。(2)基于任务的“肮脏”工作研究。随着对“肮脏”工作研究的深入,Kreiner(2006)等学者认为任何职业中都有“肮脏”的成分,“肮脏”工作研究并不应局限于特定的职业范围。这些学者开始关注工作内容中的某些“肮脏”任务,这些研究也涉及“光鲜”职业,例如,人力资源管理师(Rayner等,2014)、管理咨询师(Gill,2015)、律师(Brown和Lewis,2011)、橄榄球运动员(Brown和Coupland,2015)、投资银行家(Stanley等,2014)。由此可知,无论是工作任务还是职业,都属于“肮脏”工作的研究范畴。
3. “肮脏”工作的社会必要性
“肮脏”工作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但长久以来却被大众投以异样眼光。这些工作的“肮脏”污名常常使人们忽略其必要性和错误地看待其社会角色(Ashforth和Humphrey,1993)。Hughes(1971)将“肮脏”工作称为“社会必要的邪恶(necessary evil)”,认为“肮脏”工作是维持社会正常的功能运转所必需的,对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些工作之所以“肮脏”,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正常的社会准则。有些“肮脏”工作的社会价值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如,保洁工作、殡葬服务工作、监狱警务工作),然而,有些“肮脏”工作(如,保险推销、“狗仔队”)由于难以展现英雄主义和社会牺牲精神,其价值比较不容易被理解,但它们对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当地的经济发展仍是非常重要的(O’Donnell等,2011)。如,澳门的博彩业,虽然这一行业具有一定的道德争议,但却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肮脏”工作的社会价值不可否认,是社会所必要的,尽管有些工作可能存在道德争议(如,死刑执行、赌场工作、私人侦探)(Tracy和Scott,2006)。
(三)“肮脏”工作的分类
Ashforth和Kreiner(1999)根据“肮脏”的特征将“肮脏”工作分为身体“肮脏”工作(physical dirty work)、社交“肮脏”工作(social dirty work)和道德“肮脏”工作(moral dirty work)三类(参见表1)。这三个分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很多“肮脏”工作同时具有多个层面的“肮脏”特征(Ashforth和Kreiner,2014)。
| 类 型 | “肮脏”工作具体的分类标准 | 职业列举 |
| 身体“肮脏”工作 | 工作直接伴随令人厌恶的物质实体(如,血液、死亡者、污秽物) | 屠宰工作、护理工作、丧葬工作 |
| 工作在被认为有害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 | 消防员、高空清洁工、矿工 | |
| 社交“肮脏”工作 | 工作需要经常接触公众认为的肮脏/被污名化群体 | 狱警、精神病医务工作、社工 |
| 工作具有地位低下的仆从性服务他人特征 | 私人司机、保姆、客房服务工作 | |
| 道德“肮脏”工作 | 工作被认为会产生社会罪恶或违背社会美德 | 博彩业工作、私家侦探、文身师 |
| 工作被认为经常使用欺骗手段或有违社会礼节标准 | 讨债人员、保险推销员 |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Ashforth和Kreiner(1999)的观点整理。 | ||
Ashforth等人(2007)发现受职业声望差异的影响,“肮脏”工作对从业者的影响效果不同,职业声望高低可以作为“肮脏”工作的一个重要区分维度。因此,他们在三维度分类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声望维度,根据工作的“肮脏特征(身体、社交和道德肮脏)×职业声望(高和低)”标准将“肮脏”工作划分为六种类型(Ashforth等,2007),即高声望的身体“肮脏”工作、高声望的社交“肮脏”工作、高声望的道德“肮脏”工作、低声望的身体“肮脏”工作、低声望的社交“肮脏”工作和低声望的道德“肮脏”工作。
Kreiner等人(2006)认为所有的职业都涉及不同程度的“肮脏”,因此他们根据肮脏的广度(工作中的“肮脏”部分所占的比重)和肮脏的深度(“肮脏”的程度和直接卷入度)两个维度,将“肮脏”工作划分为高度污名(pervasive stigma)的“肮脏”工作、稀释污名(diluted stigma)的“肮脏”工作、区划污名(compartmentalized stigma)的“肮脏”工作和细微污名(idiosyncratic stigma)的“肮脏”工作四种类型(参见表2),并认为“肮脏”工作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前三种类型(Kreiner等,2006)。
| “肮脏”的广度 | |||||
| 高 | 低 | ||||
| “肮脏”的深度 | 深 | 高度污名的“肮脏”工作职业伴随着强烈“肮脏”的任务或工作环境如:入殓师、狱警 |

|
区划污名的“肮脏”工作职业中只有少数任务伴随强烈“肮脏”如:记者、律师、公关人员 |

|
| 浅 | 稀释污名的“肮脏”工作职业中有大量的轻度“肮脏”任务如:出租车司机、餐饮服务员、电话推销员 |

|
细微污名的“肮脏”工作职业中只有少数轻度“肮脏”任务如:教师、服装设计师 |

|
|
| 注:圈内阴影的面积大小和颜色深浅分别代表“肮脏”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资料来源:Kreiner等(2006)。 | |||||
以上学者的分类有助于加深理论界对“肮脏”工作的理解,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肮脏”工作对从业者认同建构以及心理和行为的不同影响。例如,Ashforth等人(2007)认为低声望的“肮脏”工作更容易面临认同建构困难的问题,因为它们缺乏“地位保护伞”(status shield)来缓冲来自于社会他人的抨击(Stenross和Kleinman,1989)。Ashforth和Kreiner(2014)指出,相对于身体“肮脏”工作和社交“肮脏”工作,道德“肮脏”工作更容易被视为“肮脏”。其理由为,相对于身体和社交“肮脏”工作“必要的邪恶”的特点,道德“肮脏”工作常被视为“不必要的邪恶”,这加深了社会公众对道德“肮脏”工作的负面感知。
三、“肮脏”工作的测量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的“肮脏”工作研究主要以理论分析和建构为主,实证研究较为匮乏。实证研究又主要以访谈、叙事等质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Grandy和Mavin,2012)。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肮脏”工作的研究发展。因此,本部分将对现有研究中“肮脏”工作的测量工具进行归纳和比较,希望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借鉴。根据测量工具的构成维度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可以将“肮脏”工作的测量划分为两大类:
(一)单一维度的“肮脏”工作测量
1. 基于主观“肮脏”程度评价的“肮脏”工作测量
基于主观“肮脏”程度评价的方法主要用于测量社会公众对工作“肮脏”的整体感知,以及对不同职业之间“肮脏”度的等级排序和比较。例如,Ashforth等人(2007)在“肮脏”工作分类结构的实证研究中,选取了30种职业(其中有18种是事先由专家团队主观判定的“肮脏”职业,包括建筑工、出租车司机、惩戒人员、丧葬服务人员、社会工作者、二手车销售人员、脱衣舞者、流产诊所护士、人身伤害辩护律师等;其余12种为几乎无肮脏特质的职业,如电气工程师、图书管理员、音乐教师、软件开发师等)进行分析。该研究将647名MBA学生作为调研对象,让他们根据“肮脏”工作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对每种职业具体的归属类别(身体“肮脏”工作、社交“肮脏”工作、道德“肮脏”工作和非“肮脏”工作四大类)以及“肮脏”度进行评分(分值从1到5,1表示非常不“肮脏”,5表示非常“肮脏”)(Ashforth等,2007)。数据显示,三类“肮脏”工作与非“肮脏”工作的均值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差异,“肮脏”度得分分别为身体“肮脏”工作3.13分、社交“肮脏”工作3.25分、道德“肮脏”工作4.10分和非“肮脏”工作1.78分,道德“肮脏”工作的“肮脏”程度显著高于身体“肮脏”工作和社交“肮脏”工作,研究所假设的“肮脏”工作分类结构得到了验证。另外,在探讨“肮脏”工作对从业者身体和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中,Baran等人(2016)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研究者让分布在各行各业的10 605名丹麦人,根据“肮脏”工作的定义,对44种常见职业的“肮脏”度进行评分(分值从1到5,分值越高表示“肮脏”度越高)。得分结果表明,该研究所关注的三类“肮脏”职业的“肮脏”度得分(屠宰场工作3.56分、监狱狱警3.78分、家政服务工作3.67分)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64分(Baran等,2016)。
2. 基于污名感知的“肮脏”工作测量
“肮脏”工作实质是一种情境化的职业污名,因此在实证研究中许多学者从污名感知视角来对“肮脏”工作进行测量。Pinel和Paulin(2005)开发了职业污名意识量表(occupational stigma consciousness,SCQ),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因此,在对电话中心服务人员“肮脏”工作污名意识和核心自我价值影响关系的研究中,Shantz和Booth(2014)沿用了Pinel和Paulin(2005)的量表。其题项包括“相对于实际情况,外部公众对电话中心服务人员有更多的负面看法”“外部公众对电话中心服务人员的判断是基于对我们的职业印象而不是我们具体工作内容的”“外部公众很难将电话中心服务人员作为平等的人群来对待”“电话中心服务人员身份会影响外部公众与我互动的方式”“当与外部公众互动时,我感到他们会根据我作为一名电话中心服务人员的身份来解读我的行为”“公众关于电话中心服务人员的刻板印象对我个人有很深的影响”(Shantz和Booth,2014)。此外,Li等人(2007)在对HIV/AIDS护理人员的研究中,也开发了5个题项的“肮脏”工作污名感知量表,样例如“由于你从事HIV/AIDS病人照顾相关工作,你遭到了外部公众的歧视”“当听说你在HIV/AIDS领域工作时,人们会在社交上远离你”(Li等,2007)。
3. 基于工作“肮脏”感知的“肮脏”工作测量
Harms(2011)等学者们根据“肮脏”工作的定义提出了工作“肮脏”感知的操作性量表。例如,在测量执法人员的工作“肮脏”感知时,Harms(2011)开发了3个题项的量表,题项包括“由于我做的工作,我对其他人看待我的方式敏感”“当我遇到陌生人时,我不想告诉他/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城市环卫工作者的离职意愿模型研究中,Kolar(2014)开发了5个题项的工作“肮脏”感知量表,样例为“我经常在不干净的地点工作”(91%赞成或强烈赞成)、“许多人不想做我所做的那些工作”(78%赞成或强烈赞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环卫工作者强烈地感到他们的工作充满“肮脏”。遗憾的是,以上研究只将“肮脏”工作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量表信效度的充分检验。
(二)多维度的“肮脏”工作测量
1. 基于Ashforth和Kreiner(1999)理论的三维度“肮脏”工作量表
Ashforth等学者(Ashforth和Kreiner,1999;Ashforth,2007)在提出“肮脏”工作分类理论模型后,没有开发可操作性量表。基于这个缺陷,Lai(2010)根据他们的分类理论,通过对800名澳门博彩业从业者的调查,开发了18个题项的三维度(身体、社交和道德)“肮脏”工作量表(perceived work dirtiness scale,PWDS)。例如,身体“肮脏”工作的测量题项有“在工作中我担心这个工作对我的生活有较少的保护”“在工作中我关心我个人的安全问题”“我的工作环境对健康是有害的”。道德“肮脏”工作的测量题项有“我的工作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的工作需要我欺骗顾客”。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聚合效度和预测效度,可作为后续研究良好的借鉴。该量表的缺点在于它是针对特定情境(赌场工作)的“肮脏”工作量表,外部信度较低,很难被其他研究所重复和比较,量表的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2. 基于Kreiner等人(2006)理论的两维度“肮脏”工作量表
有些学者根据Kreiner等人(2006)的理论,将“肮脏”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作为测量“肮脏”工作的两项重要指标。具体方法为,借助于工作的“肮脏”凸显性、“肮脏”任务的频率等指标来测量“肮脏”工作。例如,在分析动物收容所工作人员从事“肮脏”工作对离职率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就是否从事动物安乐死等“肮脏”任务(“肮脏”工作的广度)和从事这些任务的频率(“肮脏”工作的深度)来进行评价(Baran等,2012)。在对家庭护理人员角色认同的研究中,研究者所采用的测量方法是,让被调查者就具体“肮脏”任务(如帮助长者上厕所、洗澡、处理身体垃圾)经历的感知(分值从1到5,1表示非常少经历,5表示非常多经历)和具体从事“肮脏”任务的数量和时间来进行评价(Blight,2014)。但是由于文献数量有限,现有的测量工具主要聚焦于某一职业,该类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四、“肮脏”工作对“肮脏”工作从业者的影响Ashforth和Kreiner(1999)将工作内容主要被“肮脏”任务所占据的从业者称为“肮脏”工作从业者(dirty worker)。由于“肮脏”工作给从业者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长期不足,大量“肮脏”工作研究集中在“肮脏”工作对从业者的影响领域(Stacey,2005;Kreiner等,2006;Grandy,2008;Cruz,2015)。本研究主要从“肮脏”工作从业者的工作相关身份认同、工作压力和退缩行为三个方面,系统梳理“肮脏”工作对其从业者影响的研究文献。
(一)“肮脏”工作对从业者工作/职业身份认同的影响
“肮脏”工作对从业者身份认同(identity)的影响一直是该领域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Ashforth和Kreiner,2014;Brown等,2015;Simpson等,2017;Hughes等,2017)。职业是个体积极身份认同和存在价值感的重要来源(Van Dick和Kerschreiter,2016),因此,“肮脏”工作从业者必然会面对一个共同的来自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质疑,即“你怎么能从事这种工作”(Ashforth和Kreiner,1999)。对于“肮脏”工作从业者而言,“肮脏”工作在外部观察者眼中的“污损形象”使他们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威胁。“肮脏”工作从业者很难在工作领域建构积极的自我认同并获得积极的社会确认(social validation)(Ashforth和Kreiner,2014;姜海燕和王晔安,2016)。
1. “肮脏”工作从业者工作/职业身份的不认同
由于职业的负面刻板印象,“肮脏”工作从业者难以建立积极的自我感知,因而存在较高的与工作相关的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宝贡敏和徐碧祥,2006;Miscenko和Day,2016)。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肮脏”工作从业者具有较高的负面自我感知和消极职业/组织认同。例如,Lai等(2013)发现,对于赌场从业人员而言,职业的道德肮脏对职业不认同和组织不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Lai等,2013)。在一项针对电话中心员工职业污名意识的研究中,数据表明,职业污名意识与职业认同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CSE)对两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Shantz和Booth,2014)。
也有研究指出,“肮脏”工作从业者面对身份威胁所产生的与工作相关的不认同,实际上也是从业者的一种应对策略(Dutton等,2010)。在“肮脏”工作情境下,社会观念限制了从业者建构一个积极自我的可能性,为了应对负面的情绪体验,“肮脏”工作从业者借助于对工作或组织的不认同,来使他们自己远离工作的“肮脏”面。例如,当面对“肮脏”工作所带来的认同威胁时,出租车司机会选择职业疏离作为一种应对策略(Turchick,2014)。
2. “肮脏”工作从业者工作/职业身份的积极认同
尽管研究者普遍认为“肮脏”工作对从业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工作的“肮脏”污名也会对从业者产生积极作用,包括塑造有意义的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ies)和建立高凝聚力的职业群体(Ashforth和Kreiner,1999,2014;Thompson等,2003;Dick,2005;Ashforth等,2007;Drew等,2007;Simpson等,2012;Van Dick和Kerschreiter,2016)。
首先,“肮脏”工作与职业意识形态。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的是,许多实证研究发现“肮脏”工作从业者常常表现出对他们工作的赞美和自豪感(Ashforth和Kreiner,1999;Bolton,2005;Stacey,2005)。Ashforth和Kreiner(1999)认为工作“肮脏”污名威胁的存在,会促使从业者寻求有关工作意义的积极的叙事建构。“肮脏”工作从业者会通过塑造高尚的职业意识形态(如,牺牲精神、勇敢精神、仁慈精神)来缓解自尊威胁。例如,消防人员通过强调他们的工作展现的阳刚气质(强壮的、无畏的、稳健的、刚毅的和勇敢的)来建立职业自豪感(Tracy和Scott,2006)。拳击手把他们的工作视为高超拳击技术的表演(Wacquant,1995)。狗仔队记者认为他们做了名人想要他们做的事,他们的“爆料”行为只是名人提升宣传效果和知名度的一种合理手段(Levin和Arluke,1987)。惩戒人员将强制手段和暴力的使用叙述为保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合理方式(Dick,2005)。
其次,“肮脏”工作与职业群体的凝聚力。大量研究表明,“肮脏”工作有利于形成相对“强”的职业和工作群体文化。本研究将其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公众给予“肮脏”工作的贬损性、侮辱性标签,为职业区分赋予了认知基础,成为职业内群体身份认同形成的线索。共享的同一社会分类标签和社会认同压力会促使“肮脏”工作从业者逐渐形成在“同一条船上”的实体性(entitativity)(Ashforth和Kreiner,1999)。第二,根据刻板印象威胁理论,群体往往会以更为高度的认同融合来应对刻板印象威胁,共同的威胁感知有助于促成群体一致性,特别是在威胁具有对抗性时(Swann等,2009)。“肮脏”工作的污名威胁会激励当事人寻找拥有同样境遇的被污名化者或支持者,并与他们联合起来以反对歧视与不公(管健和柴民权,2011)。例如,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常常导致动物研究人员形成高凝聚力的职业社群,公开有力地表达他们利用动物作为研究对象和执行安乐死的正当性(Arluke,1991)。第三,由于“肮脏”工作从业者高污名化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支持的获取困难,“肮脏”工作从业者需要通过建立“强”职业和工作群体文化来形成“社会缓冲带”(Ashforth等,2007)。高凝聚力的职业社群是“肮脏”工作从业者拥有的一种集体资源,是群体成员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能够取用、确定和证实的有关他们工作意义的资源。“肮脏”工作从业者常借助这种集体资源来发泄沮丧情绪和获取理解性的支持行为(Tracy,2004)。例如,Sanders(2010)在对兽医助理人员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工作者中存在强职业群体文化,他们彼此分享喜欢动物这一职业意识形态,分享在工作中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他们的职业群体文化支持他们在工作中寻找尊严,群体成员之间和谐的关系也成为他们热爱工作的理由之一(Sanders,2010)。归纳而言,由于建立了高凝聚力的职业群体,“肮脏”工作从业者逐渐通过“我们vs.他们”来看待社会赋予他们的污名。他们会建立积极的职业意识形态,作为将“我们”从“他们”中区分出来的重要特质,来有力地表达他们的工作群体身份和职业身份,形成积极的职业认同(Cruz,2015)。
3. “肮脏”工作从业者工作/职业身份的矛盾认同
为了回应关于“肮脏”工作从业者对于工作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的讨论,Kreiner和Ashforth(1998)认为“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身份认同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它很难处于有意识的认同或不认同选择的两端。他们将身份认同的这种模糊机制称为矛盾认同(ambivalent identification)(魏钧等,2007)。Humphreys和Brown (2002)则将其定义为精神分裂式认同(schizo-identification),即个体同时呈现出的认同和不认同的身份叙述(Lemmergaard和Muhr,2012)。也有学者提出“贱斥理论”,将“肮脏”工作描述为“贱斥劳动”(abjection labor),即这些工作同时伴随着吸引力和排斥力(Tyler,2011)。
实证研究发现,“肮脏”工作从业者常常对他们的工作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同状态(Pratt,2000;Kreiner和Ashforth,2004)。本研究认为其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肮脏”工作从业者从客观现实中发现,他们通常很难不认同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仍需从事该工作,不认同和远离工作中的自我会使他们产生认知失调,因此很难长期维持(Costas和Fleming,2009)。并且工作的不认同状态常常会给“肮脏”工作从业者带来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和职业风险。例如,惩戒人员不得不直面工作的“肮脏”性,如果他们忽略或回避他们对“肮脏”工作的情绪反应(如,恐惧、怀疑、厌恶或排斥),他们将使自己和同事处于危险的境地(Lemmergaard和Muhr,2012)。另一方面,“肮脏”工作从业者建立积极认同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消除他们对自我工作角色的负面认知和取得他人的社会认可非常困难。以积极职业意识形态的建立为例,照料相关行业(如,护士、家政人员)相对比较容易通过“牺牲精神”来塑造职业的社会形象,而保险推销员、屠夫、矿工等却较难建构良好的职业社会形象(Chiappetta-Swanson,2005;Stacey,2005;Kreiner等,2006)。因此,环境迫使“肮脏”工作从业者常常处于对工作不能不认同,而又难以认同的两难境地。
(二)“肮脏”工作对从业者工作压力的影响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压力来自于感知的有价值资源的损失。在“肮脏”工作背景下,工作污名所带来的认同威胁和伴随着的自尊损失构成了个体潜在的和实际的资源损失(Baran等,2012)。因此,“肮脏”工作构成从业者的一个重要的压力源。本研究从“肮脏”工作从业者的消极情绪、社会歧视感知和污名管理压力三个方面来分析“肮脏”工作带给从业者的工作压力。
1. “肮脏”工作从业者的消极情绪
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肮脏”工作会引发从业者的厌恶、羞愧等负面情绪反应(Bolton,2005;Duffy,2007;Simpson等,2012),如垃圾清理和搬运工作、身体照料工作和犯罪惩戒工作(Hanser,2012;Asher,2014;Johnston和Hodge,2014)。厌恶、羞愧等消极情绪在“肮脏”工作从业者中普遍存在。这些消极情绪既来自于从业者自身的情绪反应,又来自于内化的职业污名,是影响“肮脏”工作从业者工作压力感和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Sanders,2010;Baran等,2012;Jackson和Griffiths,2014)。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人类社会“非接触文化”(non-touching culture)下,护理工作所伴随的体液、排泄物等不洁物,与病人密切的身体接触,甚至死亡接触,都会引发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动物本能”厌恶(吴宝沛和张雷,2012;Blight,2014)。针对餐饮业、美发业、出租车业等行业的研究表明,由于职业污名的存在,顾客经常以高高在上和歧视的态度对待从业者。这种服务关系的尊卑性和仆从性常会使从业者产生深深的羞愧感和无助感(Benoit等,2015)。在许多文化中,“屠夫”一词经常伴随残忍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负面形象,羞愧感和缺乏尊严感已成为屠宰人员的重要压力之一(Mccabe和Hamilton,2015)。有关社会工作和警务工作的研究也表明,职业的“肮脏”特性会直接导致从业者经历负面的羞愧、内疚等消极情绪(Harms,2011)。Perez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犯罪材料收集人员在工作中有非常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们会自豪他们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常会就工作内容产生困扰、恶心、羞愧等负面情感。当工作需要查看很多色情材料时,他们从妻子的不安情绪中感到非常羞愧(Perez等,2010)。
2. “肮脏”工作从业者的社会歧视感知
公众对“肮脏”工作从业者的社会歧视表现为,从公开的冒犯行为和语言暴力到更隐蔽的社交疏远(张宝山和俞国良,2007;Asher,2014)。Šadl(2014)有关家政人员的研究发现,雇主会通过与家政人员“划清界限”(如,尽量避免肢体接触,要求家政人员将衣服、鞋、水杯单独放置)来远离“肮脏”。许多家政人员感到他们在与雇主的交往中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雇主常常会不经意地对家政人员表示蔑视和不尊重(Šadl,2014)。Gimlin(2007)的研究表明,守门人普遍承受着社会歧视压力,许多房客将守门人称为“保安”,而不愿称呼他们的姓名,这种称谓象征性地远离了“肮脏”的“他们”,界定了房客和守门人的非人际交往关系(Gimlin,2007)。
“肮脏”工作从业者除了遭受来自社会公众的歧视,也常常遭受来自同事和家庭成员的歧视,这导致了他们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造成高工作压力。在医院系统中,一般医务人员将太平间工作人员视为死亡的象征,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人际互动中,太平间工作人员常常遭遇医院其他同事对他们工作的侵犯性提问,导致他们持续被提醒他们的工作与死亡有关的“肮脏”,这是他们工作压力的重要来源(Ashforth和Kreiner,2014)。收集犯罪材料的执法人员报告,在警务系统中,他们部门常被标识为“恶心的”,遭到歧视和疏离(Harms,2011)。此外,“肮脏”工作从业者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可能受连带污名的影响而感到羞耻,觉得跟“肮脏”工作从业者的亲密关系是一种负担,并减少对他们情感上的支持,这会进一步恶化“肮脏”工作从业者的社会支持系统(Mak和Cheung,2010)。
3. “肮脏”工作从业者的污名管理压力
为了回应社会潜在的拒绝和歧视,“肮脏”工作从业者面临一种额外的慢性压力,这种压力是关于如何进行“肮脏”工作污名管理的压力(张斌等,2013)。Baran等学者(2012)借助工作需要—资源理论来解释“肮脏”工作从业者的污名管理压力。相对于其他从业者,“肮脏”工作从业者面临更高的工作需求(如,管理职业污名),这会导致他们工作压力的增加。研究表明,“肮脏”工作的污名管理和污名应对行为会消耗个体的资源,如果污名管理所消耗的资源超过污名管理所带来的福利,污名管理对于“肮脏”工作从业者就是负面的和高压力的(Bove和Pervan,2013)。例如,对于动物收容所工作人员而言,不仅执行“安乐死”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一项令人内疚的高压力任务,而且应对“安乐死”污名同样也是高挑战性的和高压力性的(Baran等,2012)。
“肮脏”工作从业者同时也面临是否以及如何向他人隐瞒职业的污名管理压力(Frost,2011;Newheiser和Barreto,2014;Tilcsik等,2015)。“肮脏”工作从业者经常面临是否隐瞒或公开其工作特征的决策。尽管向他人隐瞒职业具有保护作用(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歧视),但污名隐瞒仍是有压力的,因为它产生了来自害怕被揭露的认知负担(彭芸爽等,2013)。
(三)“肮脏”工作对从业者工作和社会退缩行为的影响
面临“肮脏”工作污名,“肮脏”工作从业者不仅会经历一系列负面情绪,而且会展现低工作绩效、高离职行为,以及高社会疏离和报复行为(Wong等,2011)。
“肮脏”工作与从业者的低工作绩效和高离职行为存在密切关系。大量实证研究显示,“肮脏”工作与从业者的离职意愿正相关,与从业者推荐其工作给他人的意愿负相关(Wildes,2007;Walsh和Gordon,2008;Lopina等,2012;Lai等,2013)。例如,Wildes (2005)针对餐饮行业的研究发现,由于餐饮服务工作的“肮脏”污名,餐饮业服务人员仅仅将此职业作为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短暂的停靠点。高职业污名意识会显著降低员工的留职意愿,同时也显著降低员工推荐其工作给朋友的意愿和推荐其工作给自己小孩的意愿(Wildes,2005)。对女性秘书职业的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职业“肮脏”污名意识也伴随着高水平的离职意愿(Pinel和Paulin,2005)。
职业倦怠作为一种防御性压力反应经常发生在“肮脏”工作从业者身上,尤其是那些“跟人有关的工作”,如护理和社会工作(Maslachi等,1996)。对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的研究表明,“肮脏”工作本身会导致负面工作行为,以及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如职业倦怠、心血管疾病和创伤后压力失调。对于执法人员而言,“肮脏”任务(如,暴力拘捕、与罪犯紧张而危险的对峙、亲临现场或不断审视与犯罪有关的图片或影音资料)是他们想逃离工作的重要诱因(Harms,2011)。研究数据表明,许多执法人员的工作伴随着高消极情绪(包括自责、恐惧、情绪衰竭和过度警觉)和高职业倦怠症状(如感到身体的、情绪的和精神的耗尽)(Perez等,2010)。惩戒人员为了阻隔和压抑工作中的厌恶、内疚、恐惧等情绪,长期呈现出一种职业冷漠(professional indifference),呈现出工作中情绪不涉入的中立状态(Lemmergaard和Muhr,2012)。
高水平的职业污名意识还会使“肮脏”工作从业者形成一种自我挫败的社会退缩机制。“肮脏”工作从业者常常感觉到不被理解、不受认可、被鄙视和不受尊敬,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中非常小心谨慎,这种对社会公众态度的持续警惕使他们对社会交往产生焦虑和恐惧,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他们正常的社交活动(Abel,2011)。同时,感知到被社会错误指责和不公平看待,会导致“肮脏”工作从业者减少社会支持寻求行为,这会提高其社会孤立发生的可能性(赵德雷,2013)。研究数据表明,职业污名使流产医生常常遭受人际骚扰、在医疗体系中被边缘化、社会地位丧失,导致他们对人际关系充满戒心,陷入自我孤立(O’Donnell等,2011)。
五、评析和展望“肮脏”工作研究为社会心理学、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丰富现有的认同理论和污名理论研究。虽然目前研究者已围绕“肮脏”工作的概念内涵、测量以及对从业者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但是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议题仍然很多,有待研究者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深化和完善。本研究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肮脏”工作的分类和测量
由于以往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肮脏”工作的分类结构不够严谨,测量工具很难统一。尽管Ashforth和Kreiner(1999)关于“肮脏”工作的分类模型已取得普遍认同,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该分类主要由研究者通过理论建构得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学者们只提出了“肮脏”工作的分类标准,但是身体、社交、道德等“肮脏”分类指标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导致在划分“肮脏”工作的具体类型时缺乏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肮脏”工作的分类研究需要增加更多视角。根据Sefalafala和Webster(2013)的观点,工作的社会必需性、专业性、可见性、组织依存性都是影响社会公众对工作“肮脏”感知的重要因素,后续研究可以在这些维度上加深对“肮脏”工作分类的探讨(Sefalafala和Webster,2013)。
通过文献回顾,本文发现“肮脏”工作测量工具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1)“肮脏”工作测量工具的实证研究基础仍较薄弱。“肮脏”工作测量工具的开发和使用主要集中在近几年,且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已开发出来的测量工具推广程度不高,使用率较低,导致其信效度很少在后续研究中得到验证和提升。(2)在测量工具开发和使用过程中较少借助统计分析方法。未来的研究应该采用基于理论自上而下和基于实证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编制“肮脏”工作量表,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如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探讨“肮脏”工作的结构维度和提升测量工具的信效度。(3)由于“肮脏”工作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职业特征差异,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难以兼顾,这增加了量表开发难度。在实证研究中,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存在一定的对立性。由于不同职业中“肮脏”任务的表现形式存在众多差异,开发信度较高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肮脏”工作量表面临量表效度损失风险。因此,兼顾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兼顾整体职业情境和具体职业情境是“肮脏”工作测量工具开发的未来努力方向。
(二)“肮脏”工作的前因变量
从现有研究来看,“肮脏”工作污名形成的前因变量研究还非常匮乏,尤其是对组织因素的探讨还非常有限。不管是从宏观层面(社会和文化、历史沿袭和媒体),还是从中观层面(行业、组织)、微观层面(“肮脏”工作从业者的性别、种族、个性特征),对影响“肮脏”工作污名程度的因素进行持续、深入的探讨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根据“肮脏”工作的特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探讨“肮脏”工作的社会建构因素,如媒体、社会文化。根据现有研究可推测,媒体话语建构是影响工作“肮脏”认知的重要来源。媒体通过各种形式(报纸、电视、网络等)提供的有关各行各业工作的各种资讯,深深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各种职业的态度、信念与行为。媒体有关“肮脏”工作的负面描述会引导和强化公众对“肮脏”工作的污名认知。以精神病医务工作为例,Gharaibeh(2005)对美国电影的回顾发现,电影样本中有一半将精神科医生刻画成有帮助且友好的,而另一半则将其描绘为有恶意的、疯癫的、古怪的和邪恶的。第二,探讨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根据场域理论,组织情境是影响公众和从业者对“肮脏”工作污名认知的重要因素(Schneider,1998)。Grandy和Mavin(2011)研究发现,组织声望、组织支持等因素有助于提升“肮脏”工作的职业声望。也有研究表明,面对来自外部的“肮脏”工作污名威胁,员工会借助组织声望、工作特征、组织支持来对工作的正当性进行认知。当员工感知到工作特征是令人愉快的、组织具有较高的声望、组织对员工个人是支持的和关心的时,“肮脏”工作污名对员工的负面影响会降低(Tracy和Scott,2006;Roca,2010;Tyler,2011)。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将组织层面因素作为“肮脏”工作污名的前因变量和重要应对手段来进行探讨。
(三)“肮脏”工作的影响机制
从研究内容来看,有关“肮脏”工作影响机制的研究还十分匮乏,并且影响路径还不够清晰。首先,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肮脏”工作对个体情绪和心理层面的影响,较少分析“肮脏”工作对与组织绩效有关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就组织管理而言,管理者需要关注“肮脏”工作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地从与组织绩效相关的变量(如,工作动机、工作满意感、工作效能感、工作投入、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创新、工作场所偏离行为)角度探讨“肮脏”工作在组织情境中的影响机制。其次,现有的关于“肮脏”工作对从业者心理和行为层面影响的研究结论还存在许多矛盾之处(Weitzer,2010)。以自尊为例,大量研究发现“肮脏”工作伴随着从业者的低自尊( Corrigan和Rao,2012),但也有学者发现在消防员、监狱警察等群体中“肮脏”污名反而会引发高职业自豪感,从而提升自尊(Thumala等,2011)。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加强对“肮脏”工作影响从业者态度和行为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探讨,构建一个“肮脏”工作对从业者影响的综合模型,系统地考察“肮脏”工作的影响机制。
(四)研究方式方法的改进
首先,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的“肮脏”工作研究主要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较为匮乏(Grandy,2008)。“肮脏”工作研究中大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文献(Ashforth等,2007;Ashforth和Kreiner,2014)都存在只提出了研究假设,而没有进行实证检验的问题。同时,在实证研究领域,许多研究沿用社会学方法,主要采用“以文字叙述为材料,以归纳法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质性研究方法,缺乏定量分析。未来的“肮脏”工作研究应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大研究范式结合起来,相互补充。
其次,强化纵向研究和跨层次研究。“肮脏”工作污名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其动态变化既有可能表现为“肮脏”工作污名强度的变化,也有可能表现为“肮脏”工作污名感知的变化。纵向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探究清楚“肮脏”工作污名的动态发展和动态影响过程。纵向研究还有助于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不仅“肮脏”工作污名本身是动态变化的,而且其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采用跨层次研究范式,探讨不同层面因素(如,社会因素、组织因素、工作特征因素、个体因素等)对“肮脏”工作从业者“肮脏”工作感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最后,开展本土化研究。由于“肮脏”工作污名是为社会所建构的,社会文化对“肮脏”工作污名的影响非常大。“肮脏”工作污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并不陌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把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的封建观念,这在潜移默化中使得中国人对职业高低贵贱存在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择业观。在中国有许多职业被社会贴上“不光彩”“丢脸”“低人一等”“被人看不起”的标签,这样的“肮脏”标签正是导致这些职业“用工荒”困境的重要原因。遗憾的是,在中国有关“肮脏”工作的研究非常缺乏,仅有少数香港、澳门学者对中国情境下的“肮脏”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Wong等,2011;Jennifer等,2016)。因此,鉴于在中国研究“肮脏”工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将西方研究背景下的“肮脏”工作理论和实证结论放在中国本土化情境中进行考察十分有必要。未来的研究应重视中国文化(如,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对“肮脏”工作污名感知和“肮脏”工作影响机制的作用。
| [1] | 宝贡敏, 徐碧祥. 组织认同理论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6(1): 39–43. |
| [2] | 管健, 柴民权. 刻板印象威胁: 新议题与新争议[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12): 1842–1850. |
| [3] | 姜海燕, 王晔安. 承认的作用: 基于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实证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16(4): 149–158. |
| [4] | 彭芸爽, 张宝山, 袁菲. 可隐匿污名的心理效应及其机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4): 592–598. |
| [5] | 魏钧, 陈中原, 张勉. 组织认同的基础理论、测量及相关变量[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6): 948–955. |
| [6] | 吴宝沛, 张雷. 厌恶与道德判断的关系[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2): 309–316. |
| [7] | 阎书昌. 身体洁净与道德[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8): 1242–1248. |
| [8] | 张宝山, 俞国良. 污名现象及其心理效应[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6): 993–1001. |
| [9] | 张斌, 徐琳, 刘银国. 组织污名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3): 64–72. |
| [10] | 赵德雷. 污名身份对人际影响力和社会距离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3(11): 1283–1294. |
| [11] | Abel G M. Different stage, different performance: The protective strategy of role play on emotional health in sex work[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1, 72(7): 1177–1184. |
| [12] | Arluke A. Coping with euthanasia: A case study of shelter cul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1991, 198(7): 1176–1180. |
| [13] | Asher J A. Dirty work and courtesy stigma: Stigma management techniques among professionals who work with juvenile sex offenders[D].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2014. |
| [14] | Ashforth B E, Humphrey R H. Emotional labor in service roles: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3, 18(1): 88–115. |
| [15] | Ashforth B E, Kreiner G E. " How can you do it?”: Dirty work and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dent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3): 413–434. |
| [16] | Ashforth B E, Kreiner G E. Dirty work and dirtier work: Differences in countering physical, social, and moral stigma[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4, 10(1): 81–108. |
| [17] | Ashforth B E, Kreiner G E, Clark M A. Normalizing dirty work: Managerial tactics for countering occupational tai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1): 149–174. |
| [18] | Baran B E, Rogelberg S G, Clausen T. Routinized killing of animals: Going beyond dirty work and prestige to understand the well-being of slaughterhouse workers[J]. Organization, 2016, 23(3): 351–369. |
| [19] | Baran B E, Rogelberg S G, Lopina E C. Shouldering a silent burden: The toll of dirty tasks[J]. Human Relations, 2012, 65(5): 597–626. |
| [20] | Benoit C, Mccarthy B, Jansson M. Stigma, sex work, and substance u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J].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5, 37(3): 437–451. |
| [21] | Blight A C. The role identity of caregivers: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rel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dirty work, and the self[D]. Washington D 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4. |
| [22] | Bolton S C. Women’s work, dirty work: The gynaecology nurse as " other”[J].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05, 12(2): 169–186. |
| [23] | Bove L L, Pervan S J. Stigmatized labour: An overlooked service worker’s stress[J]. Australasian Marketing Journal (AMJ), 2013, 21(4): 259–263. |
| [24] | Brown A D, Coupland C. Identity threats, identity work and elite professional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5, 36(10): 1315–1336. |
| [25] | Brown A D, Lewis M A. Identities, discipline and routine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1, 32(7): 871–895. |
| [26] | Brown D J, Lian H W, Morrison R. Ostracism, self-esteem, and job performance: When do we self-verify and when do we self-enh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58(1): 279–297. |
| [27] | Chiappetta-Swanson C. Dignity and dirty work: Nurses’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genetic termination for fetal anomaly[J].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05, 28(1): 93–116. |
| [28] | Costas J, Fleming P. Beyond dis-identification: A discursive approach to self-alienation in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s[J]. Human Relations, 2009, 62(3): 353–378. |
| [29] | Cruz J. Dirty work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gender, class, and nation: Liberian market women in post-conflict times[J].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2015, 38(4): 421–439. |
| [30] | Dick P. Dirty work designations: How police officers account for their use of coercive force[J]. Human Relations, 2005, 58(11): 1363–1390. |
| [31] | Douglas M.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65–79. |
| [32] | Duffy M. Doing the dirty work: Gender, race, and reproductive labo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Gender & Society, 2007, 21(3): 313–336. |
| [33] | Dutton J E, Roberts L M, Bednar J. Pathways for posi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t work: Four types of positive identiy and the building of social resour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0, 35(2): 265–293. |
| [34] | Frost D M. Social stigm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ocially stigmatized[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1, 5(11): 824–839. |
| [35] | Gill M J. Elite identity and status anxiety: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management consultants[J]. Organization, 2015, 22(3): 306–325. |
| [36] | Gimlin D. What is " body work”?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Sociology Compass, 2007, 1(1): 353–370. |
| [37] | Grandy G. Managing spoiled identities: Dirty workers’ struggles for a favourable sense of self[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3(3): 176–198. |
| [38] | Grandy G, Mavin S. Doing gender in dirty work: Exotic dancers’ construction of self-enhancing identities[A]. Simpson R, Lewis P, Höpfl H(Eds.). Dirty work: Concepts and identities[C]. New York: Springer, 2012: 91–112. |
| [39] | Hanser A. Class and the service encounter: New approaches to inequality in the service work-place[J]. Sociology Compass, 2012, 6(4): 293–305. |
| [40] | Harms A. The dirty work of law enforcement: Emotion,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nd burnout in federal officers exposed to disturbing media[M]. Mankato: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2011: 95–132. |
| [41] | Hughes E C. 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J]. Social Problems, 1962, 10(1): 3–11. |
| [42] | Hughes E C. The sociological eye: Selected papers[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1: 66–78. |
| [43] | Hughes J R A, Simpson R, Slutskaya N. Beyond the symbolic: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dirty work through a study of refuse collectors and street cleaners[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17, 31(1): 106–122. |
| [44] | Jackson C, Griffiths P. Dirt and disgust as key drivers in nurses’ infection control behaviours: An interpretative, qualitative study[J]. 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 2014, 87(2): 71–76. |
| [45] | Jennifer G, Hu L J, Liu H J.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tigma o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older female sex workers: Results from a three-site egocentric network study in China[J].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2016, 30(1): 1–3. |
| [46] | Johnston M S, Hodge E. " Dirt, death and danger? I don't recall any adverse reaction …’: Masculinity and the taint management of hospital private security work[J].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14, 21(6): 546–558. |
| [47] | Kraus R. " We are not strippers”: How belly dancers manage a (soft) stigmatized serious leisure activity[J]. Symbolic Interaction, 2010, 33(3): 435–455. |
| [48] | Kreiner G E, Ashforth B E. Evidence toward an expand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4, 25(1): 1–27. |
| [49] | Kreiner G E, Ashforth B E, Sluss D M. Identity dynamics in occupational dirty work: Integrating social identit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pectiv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6, 17(5): 619–636. |
| [50] | Lai J Y M, Chan K W, Lam L W. Defining who you are not: The roles of moral dirtiness and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in affecting casino employee turnover inten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9): 1659–1666. |
| [51] | Lemmergaard J, Muhr S L. Golfing with a murderer–Professional indifference and identity work in a Danish prison[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8(2): 185–195. |
| [52] | Li L, Lin C, Wu Z. Stigmatization and shame: Consequences of caring for HIV/AIDS patients in China[J]. AIDS Care, 2007, 19(2): 258–263. |
| [53] | Lopina E C, Rogelberg S G, Howell B. Turnover in dirty work occupations: A focus on pre-entr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2, 85(2): 396–406. |
| [54] | Mak W W S, Cheung R Y M. Self-stigma among concealable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unified measure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10, 80(2): 267–281. |
| [55] | Makkawy A, Scott C. Dirty work[A]. Scott C R, Lewis L(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C]. Hoboken, NJ, USA: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674–680. |
| [56] | Maslachi C, Jackson S E, Leiter M P. MBI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 3rd ed. Palo Alto, CA: CPP, Incorporated, 1996: 104–123. |
| [57] | Mccabe D, Hamilton L. The kill programm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 dirty work” in a slaughterhouse[J].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2015, 30(2): 95–108. |
| [58] | Miscenko D, Day D V.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at work[J].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6, 6(3): 215–247. |
| [59] | Newheiser A K, Barreto M. Hidden costs of hiding stigma: Ironic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concealing a stigmatized identity in social interaction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4, 52(12): 58–70. |
| [60] | O’Donnell J, Weitz T A, Freedman L R. Resistance and vulnerability to stigmatization in abortion work[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1, 73(9): 1357–1364. |
| [61] | Perez L M, Jones J, Englert D R.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nd burnout among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ors exposed to disturbing media images[J].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2010, 25(2): 113–124. |
| [62] | Pinel E C, Paulin N. Stigma consciousness at work[J].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27(4): 345–352. |
| [63] | Pratt M 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ambivalent: Managing identification among Amway distributor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0, 45(3): 456–493. |
| [64] | Rayner C, Djurkovic N, McCormack D. Who are you calling " dirty”? Actors’ and observers’ perceptions of dirty work and implications for taint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rk Organisation and Emotion, 2014, 6(2): 209–222. |
| [65] | Roca E. The exercise of moral imagination in stigmatized work group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6(1): 135–147. |
| [66] | ŠadlZ. Perceptions of stigma: The case of paid domestic workers in Slovenia[J]. Teorija in Praksa, 2014, 51(5): 904–927. |
| [67] | Sanders C R. Working Out Back: The veterinary technician and " dirty work”[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10, 39(3): 243–272. |
| [68] | Sefalafala T, Webster E. Working as a security guard: The limits of professionalisation in a low status occupation[J]. 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44(2): 76–97. |
| [69] | Shantz A, Booth J E. Service employees and self-verification: The roles of occupational stigma consciousness and core self-evaluations[J]. Human Relations, 2014, 67(12): 1439–1465. |
| [70] | Simpson R, Hughes J, Slutskaya N. Gender, class and occupation: Working class men doing dirty work[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7: 367–389. |
| [71] | Simpson R, Slutskaya N, Lewis P, et al. Dirty work: Concepts and identitie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11–257. |
| [72] | Stacey C L. Finding dignity in dirty work: The constraints and rewards of low-wage home care labour[J].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005, 27(6): 831–854. |
| [73] | Stanley L, Davey K M, Symon G. Exploring media construction of investment banking as dirty work[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4, 9(3): 270–287. |
| [74] | Swann W B, Gómez A, Seyle D C. Identity fusion: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extreme group behavio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6(5): 995–1011. |
| [75] | Thompson W E, Harred J L, Burks B E. Managing the stigma of topless dancing: A decade later[J]. Deviant Behavior, 2003, 24(6): 551–570. |
| [76] | Tilcsik A, Anteby M, Knight C R. Concealable stigma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5, 60(3): 446–481. |
| [77] | Tracy S J. The construction of correctional officers: Layers of emotionality behind bars[J]. Qualitative Inquiry, 2004, 10(4): 509–533. |
| [78] | Tracy S J, Scott C. Sexuality, masculinity, and taint management among firefighters and correctional officers: Getting down and dirty with " america’s heroes” and the " scum of law enforcement”[J].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6, 20(1): 6–38. |
| [79] | Turchick H L. Professionals in disguise: Identity work in situations of downward occupational transition[R].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14, 17144, doi: 10.5465/AMBPP.2014.182. |
| [80] | Tyler M. Tainted love: From dirty work to abject labour in Soho’s sex shops[J]. Human Relations, 2011, 64(11): 1477–1500. |
| [81] | Van Dick R, Kerschreiter R. The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to effective leadership: An Overview and some ideas on cross-cultural generalizability[J]. 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2016, 10(3): 363–384. |
| [82] | Wacquant L J D. Pugs at work: Bodily capital and bodily labour among professional boxers[J]. Body & Society, 1995, 1(1): 65–93. |
| [83] | Wildes V J. Stigma in food service work: How it affects restaurant servers’ intention to stay in the business or recommend a job to another[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05, 5(3): 213–233. |
| [84] | Wildes V J.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food servers: How internal service quality moderates occupational stigm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7, 26(1): 4–19. |
| [85] | Wong W C W, Holroyd E, Bingham A. Stigma and sex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sex workers in Hong Kong[J].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1, 33(1): 50–65. |
 2017, Vol. 39
2017, Vol.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