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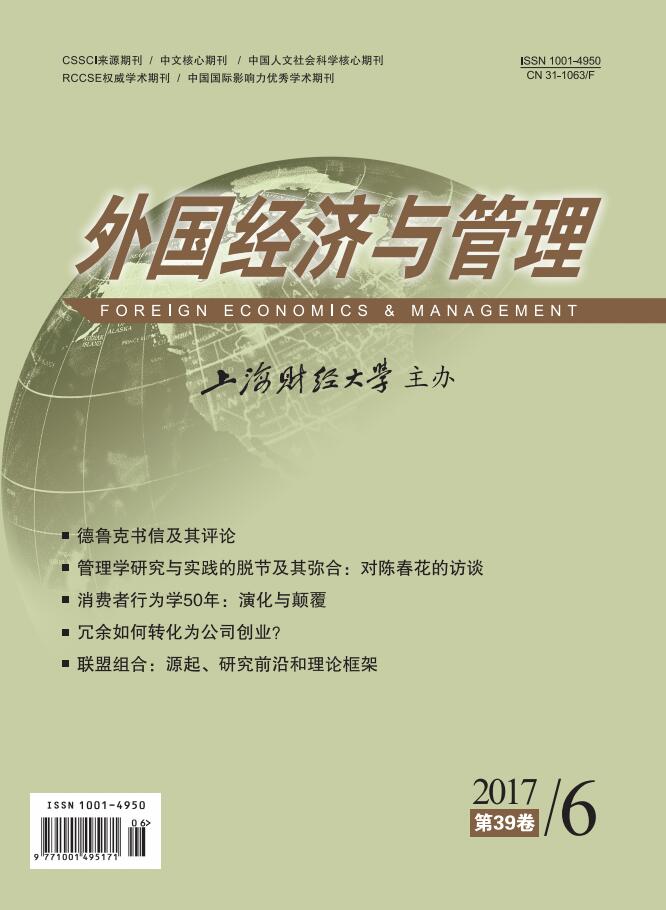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年39卷第6期 |
- 德鲁克书信及其评论
- Drucker’s letter and its comments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6): 3-11
-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7, 39(6): 3-11.

2017第39卷第6期
摘要: 本文展示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关于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的洞见和成就,由两部分组成:(1)德鲁克针对《经济学人》1994年10月1日的相关报道写给《经济学人》编辑的一封信,系全球首次公开披露;(2)知名管理学者王光丽、赵曙明、陈春花、李平团队等就德鲁克的信件所做的评论。本文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的创新有重要启示意义。
【信件】[译者:李平、杨政银]
亲爱的Bill Emmott:
非常感谢《经济学人》10月1日(1994)有关我的报道。请代我向作者转达最诚挚的谢意。
其实你可能没法想象这篇报道对我的意义有多大。这篇报道可以说是给我的最高荣誉,因为我成年之后,就一直把《经济学人》当作我的导师和学术权威。也正因如此,请允许我在此指出贵刊报道中与事实不符的一点内容。其中写道:“与其跻身于像哈佛或斯坦福这样最好的商学院,他宁愿栖身于加州的克莱蒙特学院度过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他是这所默默无闻学院里熠熠生辉的明星。”事实上,我的9部主要管理学著作中有6部是我去克莱蒙特学院之前完成的,大多在1950—1971的21年间写成。这一时期,我是纽约大学研究生院的全职管理学教授。其中有10年时间,我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兼职教授。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商学研究院,并非默默无闻的学校,更不是没有竞争力的院校。在纽约的岁月中,也就是从1950—1971年间,我从事了大量商业咨询活动。此后,我主要为非营利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尤其是教会。
至于“哈佛或斯坦福”都不只一次向我抛过橄榄枝,最终我都婉拒了。我接受不了他们的道德标准,或者说他们缺乏道德标准。这两所学校都公开大肆宣扬他们的教育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变得富有。这在我看来几乎无异于教唆男盗女娼的“法艮”(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专门教唆儿童犯罪)学校。一所商学院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唯一使命,就是教育学生,在他们的管理下让一个组织变得富有成效。这才是一所商学院应该追求的使命和目标,而不是像哈佛和斯坦福把学院的使命视为最终追求个人私利的手段。
不过这两所学校也一直限制我只能教授商业案例,限制我的咨询工作(如我的实验室)只能针对商业组织,限制我的写作内容不能超越商业管理。不过从我从事管理研究一开始,我就主张管理不仅仅是商业管理,而是定义所有现代机构的一种功能机制。直到现在,也就是我第一次这样说的50年以后,哈佛和斯坦福才愿意接受这个观点。
然而,我与哈佛以及同类学校的所谓“较劲”,其实比贵刊报道中所暗示的更甚。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比其他投稿人都多,截至目前已发表了31篇(最后一篇发表在最新一期上);第32篇将发表在1月版上。众所周知,《哈佛商业评论》直到最近一直是由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师委员会管理。多年以来,在这个委员会里一直存在激烈反对接受“那个纽约的圈外人”文章的声音。他们难以接受居然有人胆敢4次拒绝成为哈佛教授的邀请。尽管有这样的反对声音,但是鉴于我投稿文章的质量和学术价值,教师委员会最终还是每次都接受了我的投稿。
至于我在“默默无闻”的克莱蒙特学院的生涯,我是在1971年来到这里的,当时我已62岁,快到纽约大学的强制退休年龄(65岁),如果继续待在纽约大学,不久我就不能教学了,但是我只有在教的过程中才能学到东西。克莱蒙特学院同意我可以教学直到我不想再教为止。当时没有人、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待在这里超过10年。直至85岁时我仍是全职教授。
克莱蒙特学院还同意为我配备一位同事,根据我的理念创建一所管理学院。这位即将被打入冷宫、无所事事的同事由此开启了教育创新者和创业者的全新生涯。
(a)这一项目的核心不是为初级管理人员提供一个MBA项目,而是为成熟的、处于职业发展中期的人们——至少拥有15年工作经验或相应的实践经历和成就——提供一个高管管理项目。
(b)这个项目与美国当时的其他高管管理项目不同,不是一个持续几周,或最长几个月的陪衬性项目或知识方面的“员工福利”。这是一个严格和苛刻的学术项目,要求至少2年,通常是3年半到4年这样一个勤奋的持续学习过程,然后再通过严格的测试,才能得到最终的学习证书。这个项目大部分参与者最后获得EMBA学位,还有精挑细选出的合格学员再加上额外的3年时间可获得博士学位。
(c)学员一边履行全职工作,一边在晚上和周末上课。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课堂上学的东西立即运用到他们的实践中,同时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分析。
(d)最后,这个项目是管理项目,而不是商业管理项目。这意味着从一开始,我们就有意招募非商业组织的高管作为学员,这些非商业组织包括:各级政府(联邦、州、地方政府)、军队、医院、教会、学校、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等等。非商业组织的高管,占到总学员人数的1/3—2/5。
22年前我们开始这一项目时,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创的,可谓“异端邪说”。当时美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项目。但是现在,我们的项目被美国的商学院广泛地模仿,而且通常是全盘照搬,没有什么改变,比如资格最老、规模最大的商学院——沃顿商学院。我们学院不是很大,但也不是很小,毕竟有400—500个学员。我们也不想扩大规模,我们希望保持足够小的规模,以便能够进行创新、实验、变革,以使全体教师和学员能够真正地相互熟识。但是我认为把小规模与报道中的默默无闻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灯塔的灯光之所以能够很远就被看到,就是因为灯光聚焦在一个小范围内,因此使得它的亮度更高。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报道中还有一句话,无论是解读还是意见,我也不是为了批评或者纠正,我只想指出这句话是对事实的误读。报道中写道:“他一开始是大型公司的拥趸,但是现在开始盛赞小企业。”我对企业的大小从无任何偏向。我在1943—1945年间研究过通用汽车这样的超大型企业,因为我在此之前(在1942—1943年我写成的《未来工业中的人》一书中)下过这样的结论,大型公司已经变成了工业社会新的主导性的社会机构,因而没有人会关注它们,更别说研究它们。仅从这里便说我对大公司感兴趣,这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说190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伟大的Paul Ehrlich肯定赞成乱交和卖淫,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治愈梅毒药物的人。事实上,我研究通用汽车的主要结论,连同1946年我关于这一结论的书(《公司的概念》;英国叫《大生意》),以及在贵刊报道中遗漏的内容,就是大公司只有尽可能地去中心化,才能有效运转,最重要的是,才能够进行变革。换句话说,这本书主张的是小公司而不是大企业。在那时我就主张组织要尽可能扁平化,要“去层级”。然而,我在通用汽车变成“不受待见之人”(后来公司与我本人都曾公开过此事)。这是因为我在一个呈递公司高层的绝密备忘录里谈到通用汽车已经变得太大,不能最优地运转,并建议通用汽车要拆分成至少两家、最好三家相互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公司,以重新获得公司的创业动力。
但是我也不是喜欢小公司,从来就不是。我从未说过或写过盛赞小公司的话。我在1949年的书《新社会》里就写道:企业规模大小要根据功能来选择。这是我从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中很早就学到的,这本书是D’Arcy Wentworth Thompson(1860—1948)的《论增长与形式》(1917)。恰当的规模要适合组织的功能——大象要大,蝴蝶要小。事实上,过去三十年来,我为企业、医院、大学和教会提供的咨询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确定适合特定组织或机构的最佳规模。
但是从D’Arcy Thompson那里我也学到,最小而非最大的恰当公司规模可能是最佳的,这符合几何定律。过去25年来(即从1969年《不连续的时代》这本书问世以来),我一直强调,知识成为关键资源的转变及资金和信息的全球化,持续地降低了大规模的优势(顺便一提,此观点Norman McCrae也论证过,且大部分是可信的)。
亲爱的Bill Emmott,我写这封冗长的信不是为了发牢骚或抱怨,相反,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由衷地感谢您发表的报道,所以我对此感到很高兴。但是,正是因为《经济学人》的认可对我来说如此重要,而作为《经济学人》编辑的您对我的工作表现出了如此强烈和持久的兴趣,所以我想您不会介意这封澄清信——至少您肯定有一个大的纸篓可以扔。
再次:请向写这篇报道的作者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他/她为我写的故事让我感到既骄傲又开心。
祝好!
彼得•德鲁克
1994.10.12
附言:我还是不喜欢被叫做“大师”。我更喜欢这一老式但还不至于老掉牙的称呼:学生。
【评论】
呼唤“博雅管理”教育
王光丽
(香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香港)
作者简介:王光丽(1966—),女,香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
今年4月中旬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约瑟夫•马恰列洛教授受德鲁克于1994年10月给《经济学人》编辑Bill Emmott一封回信的内容启发,写了《A Year with Peter Drucker》(中文译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一书,让我对这封信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德鲁克在这封回信中,主要就《经济学人》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进行澄清,尤其是他对大学教育理念的看法,他研究管理的使命,以及他创建高级管理人员管理课程的洞见等的阐释,晶莹剔透,掷地有声,贯彻了德鲁克一向的睿智、洞察、大胆和真诚。看完后感觉十分震撼。他所提出的问题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环境仍十分相关,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当今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思考管理教育的方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传统智慧早已道出大学教育的真谛。大学的宗旨是培养塑造具备高尚品德、追求真理、贡献社会的人才;管理教育更应是培养有责任心、使命感、对未来社会发展有承担的管理者。在这封信中,德鲁克毫不隐晦他对“哈佛、斯坦福”以前有过的教育理念很不认同。在他眼里,背弃大学育人的宗旨,而公开宣扬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将学生变成富有之人,无疑体现伦理道德沦丧。德鲁克凌厉痛斥的笔锋背后,隐含着他对这些殿堂级大学迷失的切肤之痛,同时也反映了他深切的担忧。
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德鲁克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研究管理并创建了这个学科,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管理减少社会因变革和动荡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他认为管理是关于人的活动,因此管理者需要洞察人性,管理者在做出任何选择的背后都离不开价值观、承诺和信念的支撑。因此,管理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脱离实际的人文修养学科,而是一门技艺,让劳动者释放善意和潜能,自由创造利于社会的成果,并在这个自由创造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和能力。德鲁克把它界定为“一门真正的博雅艺术(A truly Liberal Art)”。纵观德鲁克一生的工作,他研究管理的使命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基于他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不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管理实践达至卓有成效,绽放出生命的光彩,实现做人的意义。
德鲁克的“博雅管理”思想,影响着一代代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引用了很多成功的实证。很多杰出的管理者和管理大师尊称德鲁克为导师,感谢他的启发令他们思考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环顾当代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公司,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他们成功的背后都投射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利他思想和真诚共享的创富理念。德鲁克“博雅管理”的思想正在被广泛传承。
今天无论是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有一真理恒久不变,那就是人类对美好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一个关爱的社会,任何成功创造客户价值的企业,他们的工作最终都会回归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社会长远进步发展的承诺,这也是德鲁克“博雅管理”的本质。“提问正确的问题”是21世纪成功的关键,管理者所做出的选择需经得起良知的验证和时间的考验。“提问正确的问题”最终可以带领我们走向通往真理的大门。
德鲁克这封信也提醒我们再次审视德鲁克管理学院的使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德鲁克学院是德鲁克生前亲自授权、唯一以他名义在中国成立的管理学院,目的就是为中国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深信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里成长的人才,才最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过过去十几年的努力,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管理者通过德鲁克学院学习德鲁克的管理实践理念。近两年,德鲁克学院在香港成立了德鲁克实验室,专注研究“博雅管理”教育与实践。我们通过与海内外著名院校合作,致力于让“博雅管理”教育再次走入大学的学历教育,尤其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的年轻学子在大学期间及时接触到“博雅管理”的理念,成功开启他们通向东西方智慧的大门。
德鲁克这封信有机会能与中国的广大读者⻅面,在此特别要感谢李平教授。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他的博士生一起完成翻译工作,旨在推动“博雅管理”教育与实践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我们衷心希望更多中国的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推动“博雅管理”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德鲁克:管理学中的一座灯塔
赵曙明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作者简介:赵曙明(1952—),男,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不确定性和风险可能是当今管理实践的最大挑战。在管理研究领域,我们究竟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未来的职业管理教育走向何方?这可能也是每个管理教学研究者的最大困惑。今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教授1994年写给《经济学人》主编的信件从尘封中开启,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先生高瞻远瞩的管理思想。读罢“Peter Drucker,Salvationist”一文及德鲁克教授的郑重回复,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先生对当代管理学实践与MBA教育的前瞻性思考和洞见。
管理:社会组织的基本器官与功能
《经济学人》将德鲁克先生称为布道者。顾名思义,布道者常常先于常人洞察商业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趋势。由于他早期受到波兰尼思想的影响,他很早就认识到工业社会中知识价值的巨大变化。在知识社会来临的前夜,他预见到成员与组织、知识与资本、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重大转变。他率先提出了企业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系统,更是一个社会系统。管理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企业获利或个人致富,还有更崇高的使命。他从早期研究营利组织(公司),后来研究非营利组织(政府、学校、医院),到最后研究社会组织(社区、社会)。这也是德鲁克本人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原因。事实上,他最初首要的管理兴趣正是始于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他的很多著作是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的。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正如德鲁克在1999年1月撰写的“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中指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早在60年前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很多人都认为,德鲁克教授的真知灼见是他丰富的企业实践、咨询经验的总结。在信中,德鲁克教授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作为管理理论研究者和构建者的定位和思考。他列举自己1950—1971二十余年间管理学研究与实践的累累硕果。其中包括了6部管理学专著问世,执教于全美最大两所商学研究院(全职和兼职)以及提供商业咨询工作等,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30多篇论文。他坦率地承认,多次拒绝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顶级商学院的邀约是由于教育伦理观不一致。他一直认为,自己只不过采取了与学术界不同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实际上,他一直更愿意称自己为“旁观者”。德鲁克认为,他教授的并不仅仅是商业案例,他的咨询工作与管理学专著并不局限于商业组织的范畴。他认为,自己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并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门学科,尤其是围绕责任。
MBA教育:知行合一的学习系统
德鲁克教授并不赞同“Peter Drucker,Salvationist”一文对他职业辉煌期与幽暗期的划分。先生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在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职业生涯,并深深为之自豪。他于1971年开始任教于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直至辞世仍心系教学、笔耕不辍。吸引他加入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是,学校答应以他的教学理念建立一所管理学院。
他希望以创新的理念和方法建设一所小规模、别具一格的管理学院。其核心观点包括:(1)MBA项目是面向较成熟的中层管理者的教育。(2)不同于其他的管理培训项目,它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术学习之上,学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3)学员们要即刻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再把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带回课堂,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正如他所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4)管理学习应该定为小规模、创新和变革。与德鲁克教授的管理学定位相呼应,MBA的教学规模要适度。只有规模适度,才能保证管理者之间、管理者和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管理教育应该在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搭建相互学习的桥梁。学生应该既从企业中吸收,同时也要从政府、军队、医院、教会、高等院校、非营利社区中来。既要能促进创新、实践、变革,还要保证学生和教师能互相了解。在项目创立之初,德鲁克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不为主流商学院接受,但是后来却被广泛复制,甚至得到全美最大、最古老的沃顿商学院认可。
非营利组织研究:组织规模和生命认识的深化
到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任教期间,他的主要研究课题都是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现代商业企业要持续生存下去必须向非营利组织学习。学习非营利组织如何以责任、价值和使命为服务宗旨构建组织的形态。同样,非营利组织也应该向商业组织学习。学习商业组织的效率、成本和收益。他认为MBA项目并不仅仅是个商业管理项目,应招募各行各业的学员,其来源包括政府、军队、医院、教会、高等院校、非营利社区等。只有让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学生一起学习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信中,德鲁克教授着重厘清了他关于组织规模的观点,并详尽论述了组织规模认知深化的过程。首先,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鲁克研究了大型组织——通用汽车公司,并在《未来工业中的人》(1942—1943)中指出,大规模组织结构已成为工业组织的主要形式。但事实上,人们却忽略了德鲁克先生对大型组织的分权管理与扁平化发展的主张。其次,到了1949年,德鲁克教授在《新社会》中指出,组织规模是否适合无关大小,而在于其功能的实现。
《经济学人》文章里说,“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必定是彼得•德鲁克”。而先生却低调地回应,他是一名学生。在我的印象中,德鲁克其实并不希望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只喜欢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彼特”。尊敬的彼得•德鲁克教授创造出影响整个世界的管理理论和思想,它犹如一座灯塔,同时照亮了东西方世界;又犹如一壶醇酒,穿越时间,历久弥新。报道和信笺之间,德鲁克教授对管理学的贡献可见一斑。
先生对MBA教学理念和运行模式的独特思考一直深深地影响并激励着我。在任职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十五年间,我始终沿着先生的足迹为办好中国的MBA教育、培养各行各业的杰出管理者而不懈努力。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虽然他远在大洋彼岸,甚至2005年11月11日已经离世,但他的思想却跨越时空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德鲁克先生的价值贡献
陈春花1,2
(1.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2.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陈春花(1964—),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管理学讲席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1954年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的问世则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正是德鲁克创建了管理学这门学科。2005年11月28日的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是:“彼得•德鲁克:发明管理的人。 为什么彼得•德鲁克的思想仍然重要?”
今天,彼得•德鲁克1994年写给《经济学人》主编的信首次公开面世,展现在读者眼前,让我们再一次沐浴到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光芒。读罢“Peter Drucker,Salvationist”一文及德鲁克的信件,我再次感受到德鲁克先生给予管理学者的巨大帮助:如何贡献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的价值。
管理研究:解决实践问题
德鲁克先生的真知灼见是他丰富的企业实践、咨询经验的总结。在信中,他列举自己1950—1971年间从事管理学研究和实践的累累硕果。这一时期,他完成了自己9部主要管理学著作中的6部;这一时期,他是纽约大学研究生院的全职管理学教授,其中有10年,他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兼职教授;他的主要商业咨询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样的研究路径,让德鲁克的著作承载着其极具旺盛生命力的管理实践思想。
德鲁克先生认为,管理研究要解答实践问题。能提出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是管理学进步的标志。在其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德鲁克回答了管理实践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管理作为独特的组织活动如何设定自己的结构?管理中如何面对人?管理决策的依据是什么?管理的范围如何界定?管理实践界定的标准是什么?管理的成效如何评价?当德鲁克先生清晰、准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的时候,管理实践所取得的成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项创新。
管理教育:必须知行合一
阅读德鲁克先生的信,我第一次知道克莱蒙特学院德鲁克管理学院的缘起。在这之前,因为导师赵曙明教授毕业于这所大学而有所认识,但是并不知道原来是德鲁克依据自己的理念亲手创办了这所管理学院,并且让一位“即将被打入冷宫、无所事事的同事”“开启了成为成功教育创新者和创业者的全新生涯”。看到这些,真是出乎意外的惊喜。我觉得,管理教育就应该如德鲁克先生所设计的那样,让管理者“可以把课堂上学的东西立即运用到他们的实践中,同时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分析”。
德鲁克在克莱蒙特学院的管理教育实践,也体现了他对于管理本质的一贯的理解,就是“知行合一”。德鲁克自己就是“知行合一”的典范,虽然他所创立的教学项目在当时不被主流商学院接受,但是他坚持要为学生“贡献”价值,坚持“保持足够的小规模,以便能够进行创新、实验、变革,以使全体教授和学员能够真正地相互熟识”,最终,其创设的管理教育被广泛复制,甚至得到沃顿商学院的认可。
管理学者:拥有创新精神
阅读德鲁克的信件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看到德鲁克先生满满的“创新精神”。他不断关注管理实践创新,并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新的管理理论和思想。例如,他研究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组织,主张大型组织要尽可能地扁平化、“去层级”,并建议通用汽车拆分成至少两家、最好三家相互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公司,以便让其重新获得“创业动力”。再如,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预见到,知识将成为关键资源,信息全球化将削弱大型组织的规模优势。德鲁克先生敏锐的前瞻视野和充沛的创新精神令人赞叹。
德鲁克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提升现代社会中非营利组织机能的重要,于是将其管理咨询和管理教育延展到非商业领域。他早期主要从事商业咨询,而在后期,他将咨询工作的中心转移到非营利机构、尤其是教会。他在克莱蒙特学院所设立的课程,来自各级政府、军队、医院、教会、学校、社区服务中心等非商业组织的高管学员,占到学员总人数的1/3—2/5。
结束语: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
“比使命更重要的是实践”这句话是我总结德鲁克先生经典著作价值贡献一文的结束语。在点评先生的信件时,我忍不住还是用这句话做结束语,但是改动了一个词: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我们一直在思考德鲁克思想的旺盛生命力的来源,最后发现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就在于,作为旁观者的德鲁克的思考是如此地贴近管理实践的真实情况,以至于后人的所有优秀作品的重要观点几乎都可以从其思想中找到根源。
德鲁克的思想可以被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所接受并且应用于不同的领域,正是源于他对于管理本质的界定:“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对于每一个管理学者而言,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就像德鲁克先生倾力实践他的使命一样。
融会贯通:“德鲁克之路”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
周云杰1,李 平2,杨政银2
(1.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作者简介:周云杰(1966—),男,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尔集团总裁;
李 平(1957—),男,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终身教授;
杨政银(1985—),男,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国内管理学界近来就管理研究的价值取向、范式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但争论中涌现的共识是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差强人意,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寥寥。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管理研究逐步与西方主流研究标准“接轨”,却与中国管理实践渐行渐远。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与恢弘蓬勃的中国管理实践不相匹配,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反思。
在中国管理研究自身亟须转型升级的岔路口,回顾“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管理学研究之路具有独特意义。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影响力毋庸讳言,他的伟大成就更多地来源于他的管理思想对管理实践的巨大影响力。如果按照现行学术评价标准,绝少发表学术性论文的德鲁克,不太可能在商学院生存。然而,德鲁克凭借其对管理的深刻洞见取得了可能比其他任何“主流管理学者”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独特影响。重温“德鲁克之路”,就是把他的经历当成一面镜子,一方面映照出国内管理研究界的现状,另一方面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出路折射出一束光亮。
管理研究的根本使命是为社会组织管理的改进提供有效的启发与指导,其根本目的是追求研究影响力。概括言之,研究影响力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做出纯研究的理论贡献;二是为教学提供素材;三是对管理实践具有启发与指导意义。这三者并非天然彼此独立分离,而常常是一体三面,相互融合与促进。只是具体到研究者个体,并不一定每人同时具备,可能是三者选其一或其二;此外,三者同时具备的少数研究者在三者具体比例结构方面各有侧重。比如德鲁克的影响力主要在于第三以及第二点,而马奇的影响力则主要在第一和第二点。不言而喻,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三者兼顾,这就必须追求理论与实践,东方与西方这两大维度的融会贯通。
与个体研究者不同,对于整个管理研究社区而言,以上三个层面则是必须同时兼顾,缺一不可。尤其是作为一门职业性学科(如同工程学,医学和法律学,但区别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管理学对管理实践的启发与指导是检验其研究成果不可或缺的标尺之一,无论是短期或长期的衡量标准。如果一项管理研究成果与实践始终关联不大,甚至毫无实践启发意义,此类研究就有严重缺陷。
德鲁克是一位在管理实践与教学领域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大师,而马奇则是在管理学术研究方面有着卓越影响力的大师。虽然他们二人走的路径不同,但都在管理领域创造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们殊途同归。我们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时兼顾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融会贯通,相当于将德鲁克与马奇集于一身!虽然对于研究者个人,这几乎不太可能,但对于整个管理研究社区,这却是可能且必须的。因此,管理研究者个体应该尽量努力兼顾理论与实践,因为这是管理研究的最佳路径;作为管理研究社区,研究(包括教学)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德鲁克之路”启示我们,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须走“知行合一”之路。“知”代表管理研究,而“行”代表管理实践,这两个领域只有“合一”,甚至“不二”,才能让管理成为社会的基本“器官”,这也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最佳模式。特别值得指出,德鲁克管理思想与王阳明心学高度暗合:德鲁克认为管理是激发人的潜力,王阳明则提倡“致良知”;德鲁克强调管理的实践性,王阳明则注重“知行合一”;德鲁克重视目标管理,尤其主张为顾客创造价值,王阳明思想则在近代日本被解读为“义利合一”(这在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方面,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不仅是一名企业管理者,更像是一位理论研究者。作为德鲁克的忠实粉丝,张瑞敏经常引用德鲁克的经典理论,如“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张瑞敏在海尔提出了“人单合一”理论模式,其实践让中国企业走到了世界管理的前沿。在此模式中,“人”是创客(员工及合作者)的独特追求(自我实现),“单”是用户(已有用户及潜在用户)的独特需求(体验),“合一”就是创客与用户互动互惠,特别是让每位创客成为自己的CEO(正如德鲁克所言),在为用户创造体验价值的同时创造自我价值,从而实现利他利己的融会贯通(这正是“成就感 ”的完整意义,既成就他人,也成就自我)。海尔用12年的时间(2005—2017年)潜心实践这个理论模式,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这一模式不仅成为国内外各大商学院争相研究的管理实践典范,也为中国管理理论创新开创了引领世界的先河。
基于这样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我们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既要“顶天立地”,也要“东西融合”。“顶天立地”指“顶”中国传统哲学的“天”,“立”中国管理实践的“地”,即扎根于中国管理实践的沃土,并探究其背后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理念的根源,从而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东西融合”指贯通西方的管理理论及方法与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及实践。换言之,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正是构建源于中国本土又有世界普适性管理理论的两大最为有效,并且相互依赖的进路,两者共同构成中国本土原创管理研究的康庄大道。
 2017, Vol. 39
2017, Vol.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