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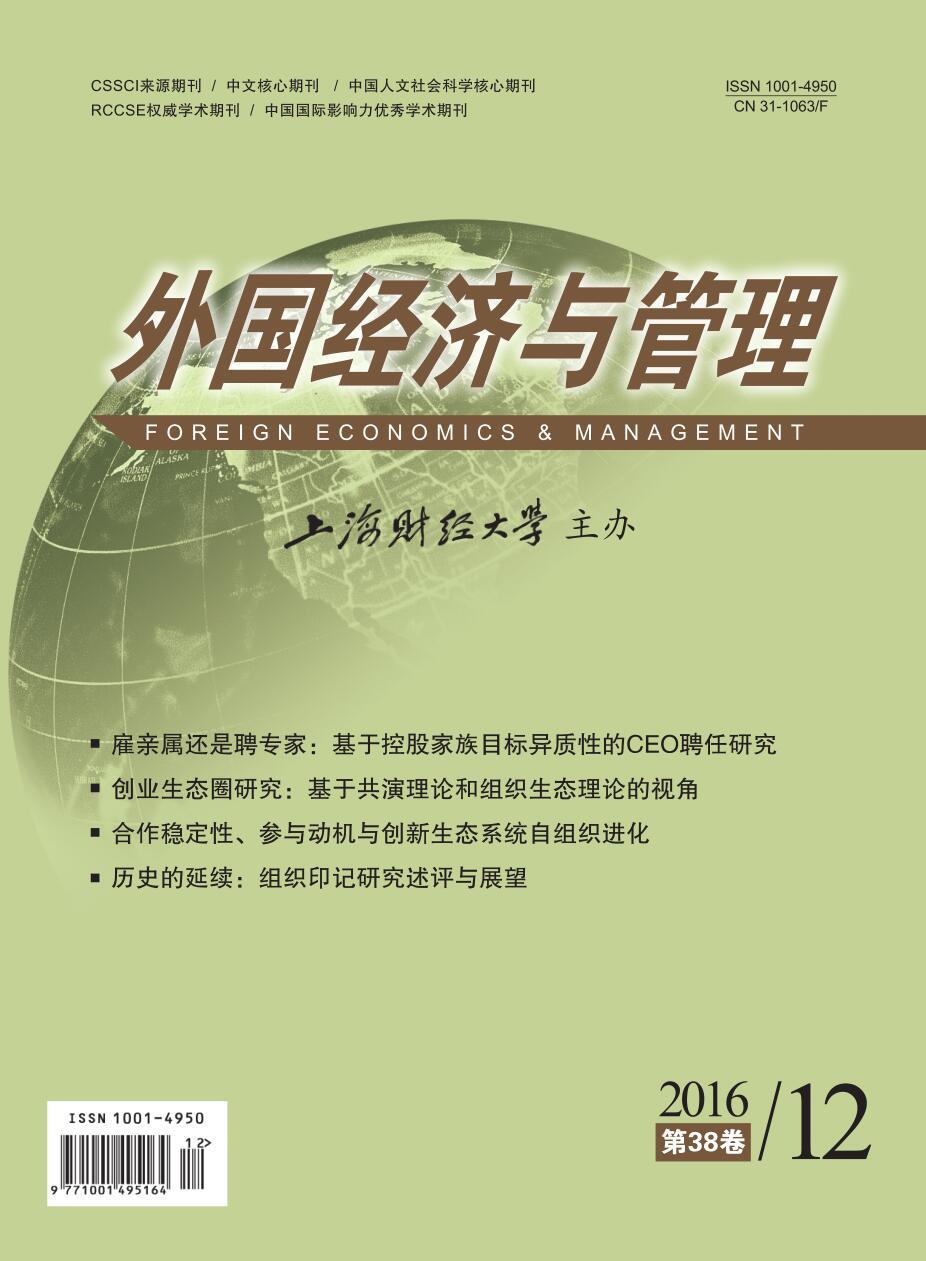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年38卷第12期 |
- 翁清雄, 王婷婷, 吴松, 胡海军
- Weng Qingxiong, Wang Tingting, Wu Song, Hu Haijun
- 情感型领导:量表开发及与员工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关系
- Affective Leadership: Scale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s and Voice Behavior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12): 74-90
-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6, 38(12): 74-90.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6-02-17

2016第38卷第12期
2010年,震惊中外的“十三连跳”将富士康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富士康公司机械化的工作制度、缺乏情感交流的成员关系以及“逼迫式”的工作强度等问题引起了无数人的声讨。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通用电气坚持以人为本,怀揣着一份关爱之心真诚对待每一名员工,深入员工的内心世界,调动员工的情感积极性,因此公司内部气氛和谐、关系融洽,在外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这些企业的管理实践告诉我们,当今社会,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因素中,员工的情感因素不容忽视,这也对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分析传统管理存在的困境,齐善鸿和邢宝学(2011)指出,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需要,因此要想发挥管理的预期作用,建立管理主客体之间和谐的情感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Newman等(2009)也认为领导并不仅仅只要实施认知或理性行为,很多时候也需要付出情绪劳动,并且需要通过艺术性方式表达情感。他们发现要想提高管理的有效性,管理人员面临的挑战不是提高工作效率,而是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加人性化和具备人文关怀。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淡化领导权威而重视建立组织中领导与成员之间良好人际关系的领导方式即情感型领导(affective leadership)逐渐受到推崇。
虽然早有西方学者认识到情感对于领导有效性的作用(如,Ashkanasy和Tse,2000;Brown和Keeping,2005),但是迄今为止,关于情感型领导的研究仍十分缺乏,尚没有实证分析。这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是过去几十年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主流文献提出的领导风格进行分析和检验,非常缺乏对扎根于东方文化的领导风格的提炼和探讨;二是情感型领导研究还仅仅停留于经验性和理论性探讨,尚缺乏开展实证性研究所需的量表。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对情感型领导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探析其结构维度,并按照规范的方法编制一套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量表。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检验所开发量表的区分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以进一步验证其结构的合理性,并证实情感型领导的有效性。本研究选取了参与型领导(participative leadership)、工具型领导(instrumental leadership)和支持型领导(supportive leadership)三种风格的领导作为效标,以检验情感型领导与这三类领导的区分性。同时,基于以下考虑,我们选择员工的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作为效标以检验情感型领导的有效性。
领导与员工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能够增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帮助组织有效地留住核心员工(厉凌和陈同扬,2010)。很多研究都表明,员工与领导者之间的认同感、信任以及相互支持可以提升员工留在当前组织的意愿(Kumar Mishra和Bhatnagar,2010;Tse等,2013)。情感型领导重视与部属之间情感的建立,通过对部属情感上的关心和唤起,来使部属对领导和组织产生情感上的依赖,最终达到留住人才的目的。鉴于此,研究二选用离职倾向作为效标来检验情感型领导对组织所关心的员工重要行为的预测作用。
研究表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各层级员工的建言行为(Morrison,2011)。但是,建言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很多时候员工会选择沉默(Van Dyne和LePine,1998)。而情感型领导的主动关怀和善意引导可以在领导与部属之间建立信任,展现领导的开放性,拉近领导与部属的距离。根据以往关于领导与部属间信任、领导开放性与建言行为关系(Detert和Burris,2007;Gao等,2011)的研究文献,我们预期情感型领导可以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因此,我们选择建言行为作为另外一个效标来检验情感型领导的有效性。
二、 研究一:情感型领导的概念和量表开发 (一) 情感型领导的理论基础和多维结构Derue等(2011)提出了影响领导效能的特质—行为模型,认为影响领导有效性的领导行为主要包括任务导向型、关系导向型、变革导向型以及负性领导行为这四类。根据模型中四种领导行为的界定,情感型领导行为对应于关系导向型领导行为,它重点关注组织中人际关系的建立,期望通过触及员工情感层面的需求来激发其积极态度和行为。下文先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对情感型领导进行理论基础的探讨,然后基于此提出情感型领导可能存在的结构维度。
1. 情感型领导的理论根源有研究表明领导行为的有效性与文化存在较大关联(Gelfand,2007),所以要研究领导,有必要考虑文化的作用;而要研究关系导向型领导行为,则有必要深入探究文化背景中有关人际交往的文化因素。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重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各项礼仪规范,包括领导与部属之间。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明夷待访录•原臣》)。类比到现代社会,这个比喻意指领导与部属之间应当是一种人格上相互平等,职权和职责上分工合作,精神和情感上亲密默契的关系。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是经营管理之道(刘小华,1996),对于创建和谐型组织,全面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王椿阳等,2006)。“仁”的核心是爱人,对他人表现出同情、关心和爱护(《尚书》);“义”就是表现出正义、公平和无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履行道德义务,主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礼记•中庸》);“礼”就是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建立良好的道德关系和有序安定的社会秩序(《荀子•劝学》);“智”表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及他人的道德本性(《论语•宪问》);“信”指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论语•学而》)。
总而言之,儒家“五常”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的作用或者说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也映射到了我们所有的人际互动中。
2. 情感型领导的多维结构基于对儒家“五常”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关系导向型领导风格,情感型领导的行为模式有迹可循。具体而言,表现出“仁”的领导者会爱护、关心和帮助部属,设身处地为部属考虑;重视“义”的领导者在部属遇到困难时,会积极给予帮助,支持部属完成工作;以“礼”待部属的领导者注重道德修养;“智”的领导者具备较高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水平,能够明辨部属以及部属之间的情绪状态和情绪变化,并有能力进行调节和处理;重视“信”的领导者对待部属言行一致、信守诺言(刘兵等,2014)。其中“礼”和“信”更多强调的是领导者个人的品质和修养而不是行为,所以本文将分别从“仁”“义”“智”三个方面分析情感型领导可能的行为表现。
仁爱的领导关心部属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和情感需要,宽以待人。其行为类似于家长式领导中的仁慈领导(benevolent leadership),比如都会关心部属在工作中的情感体验,还关心其家庭和情感问题等,并且都会表现出对部属的宽容和保护。但二者有不同之处:仁慈型领导对部属的施恩建立在部属的忠诚之上,如果部属忠诚,即使他们工作表现较差还是会持续雇用他们(郑伯埙等,2000);情感型领导对部属的关爱和关怀不是以部属忠诚为前提的,他们期望通过对部属的关怀来提升部属的幸福感以及部属对组织的感情和信任。
仗义的领导除了关心工作之外还会关注部属个人的发展及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这与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个性化关怀有一些共通之处,都是指领导尊重和关心部属期望获得发展和成功的需要和欲望(Avolio等,1999),并且有时候领导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对部属给予支持。不过,二者也存在差异,变革型领导的个性化关怀主要关注员工工作层面的成就和成长需求(陈永霞等,2006),而情感型领导则超出工作之外,还会关心部属的个人问题,包括家庭情况和情感生活等。
情感型领导的“智”主要体现在对部属的情绪管理上,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而且注重对员工情绪的管理。他们注重对部属情绪的观察、调节和管理,注重提升部属在工作中的积极情绪,进而使部属产生较高的工作积极性和组织承诺。一些已有的领导理论也已经注意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例如,Barbuto Jr和Wheeler(2006)强调了领导者对部属情绪管理的重要性,认为情绪抚慰能力是一个有效的领导者最应当具备的管理技巧之一。Goleman等人(2001)将情绪智力与领导力结合起来,指出“情绪智力是最根本的领导力”。
综上分析,情感型领导在概念上具有潜在的多维结构,可能包含仁爱、仗义和善于管理情绪三个方面,其实际结构维度需要通过规范化的量表编制流程来确定。
(二) 情感型领导量表的编制过程考虑到情感型领导的结构维度存在多种可能,根据Hinkin(1998)关于量表编制的方法指南,我们采取以下几个步骤来编制量表的题项:
1. 条目生成(1)开放式访谈。我们(含1名教授、1名博士生和2名硕士生)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MBA在职周末班的18名学员进行了访谈,访谈主题是“您认为什么样的领导是情感型领导”“情感型领导具备哪些行为特征”等。此外,我们还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相关信息。
(2)数据编码,形成题项。对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所得材料进行整理、编码、归类和汇总,并参考已有相关量表的题项,编写情感型领导量表测量题项,形成64条语义较为明确的描述性语句。
(3)表面效度分析。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在读管理学博士生和硕士生总共14人参与了题项的修订,确保题项语义明确,并有良好的可读性。经过词义的修订、合并和删减,剩下34个题项。
(4)内容效度分析。将初步形成的量表题项乱序排列,请46名MBA在职周末班学员勾选能反映情感型领导的题项,再依据选择频次进行题项删除。最终删除了14个题项:其中8个(如,“他待人总是很热情”)描述的是领导的个性特征或者人格特质,并不能确切描述领导行为;另外6个(如,“他很注重诚信”)描述的是领导的职业道德方面,不是情感型领导所特有的行为。此外,1名管理学教授、4名管理学博士生以及8名管理学硕士生对内容效度进行了二次分析,删除了可能存在跨维度效应的4个题项和1个与其他题项很类似的题项。
(5)预试。预试采用网络问卷法进行,将形成的15条目问卷发放给前期访谈对象并委托其邀请8~10名同事参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36份。问卷采用Likert 5点法计分,1~5分分别表示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及非常符合。
对预试的结果进行初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初步编制的量表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二维结构,而不是三维结构,可能是因为“仁爱”和“仗义”存在较大的共性,描述的都是领导对部属的支持和帮助,可以合并为一个维度进行考量①。此外,其中有3个条目共同度偏低(在0.40以下),说明这些题项对所属的维度解释性不够,故将其删除。最后形成了一个包含12个条目的情感型领导正式量表,每个题项都要求被试回忆其直接领导的一贯行为,然后对领导行为与题项的相符程度进行打分。
孟子在弘扬“义”时也将“仁义”并称;仁乃义之源,义乃仁之体(成中英等,2014)。
2. 探索性因素分析(1)测试对象
本研究在网上先后发布了两次问卷,测试对象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在职周末班的学员及其同事。对于有效问卷的填写者,给予30元现金奖励。第一次发出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192份:其中男性占64%;年龄在25岁及以下、26~30岁、31~40岁和41岁及以上者各占22.0%、40.0%、24.1%和13.9%;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各占6.9%、25.0%、56.0%和12.0%;具有专科及以下、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各占6.6%、51.2%和42.2%。第二次发出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166份:其中男性占68.1%;25岁及以下、26~30岁、31~40岁和41岁及以上者各占19.3%、38.6%、24.1%和18.1%;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各占10.8%、26.5%、53.0%和9.6%;专科及以下、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各占10.2%、49.4%和40.4%。
根据Hinkin(1995)的建议,两部分样本分别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两部分样本在性别、年龄、职级、学历等基本变量的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对数据的项目分析结果显示每一个条目都具有较高的鉴别度,能够有效区分高分组和低分组(Babbie,2012)。
(2)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第一次回收的数据样本(N=192)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检验值为1 955.87,p<0.000,说明各条目之间有共享因素的可能性。而样本的KMO值为0.89,说明样本数据适宜做因素分析。其次,对问卷的12个条目进行一阶因素分析。因子抽取选择主成分抽取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因子旋转选择Promax斜交旋转法。结合碎石图,共抽取出2个因子。最后,根据因子载荷的大小对条目进行删除。在本研究中,12个条目在对应维度上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50,在其他维度上的载荷都小于0.50,且不存在载荷差小于0.2的情况,如表 1所示,2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72.92%,比较理想。
| 条目 | 因子载荷 | |
| 情感关怀 | 情绪管理 | |
| Q1当部属偶尔未能完成工作任务时,他会尽量从宽处理 | 0.96 | -0.18 |
| Q2他会创造宽松的环境以便部属诉说不满 | 0.91 | -0.01 |
| Q3部属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他会主动给予支持 | 0.88 | -0.01 |
| Q4他会主动了解部属工作上的困难 | 0.79 | 0.06 |
| Q5部属的生活遇到困难时,他会主动给予支持 | 0.73 | 0.13 |
| Q6在布置工作任务时他会先征求部属意愿 | 0.72 | 0.09 |
| Q7他对部属的生活质量好坏非常关心 | 0.70 | 0.19 |
| Q8他总能察觉团队成员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 -0.13 | 0.93 |
| Q9他擅长处理部属的负面情绪 | -0.02 | 0.90 |
| Q10他总是能留意到部属情绪的变化 | -0.02 | 0.86 |
| Q11他有能力调节部属间的冲突 | 0.14 | 0.78 |
| Q12与人交谈时他善于调动对方的积极性 | 0.12 | 0.76 |
| 解释变异(累积72.92%) | 62.13% | 10.80% |
| 内部一致性信度 | 0.93 | 0.92 |
| 折半信度 | 0.91 | 0.86 |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前文探索得出的二维结构,根据对应条目的内容分别对两个维度进行命名。第一维度为“情感关怀”,是指领导对部属工作和生活的关心和协助程度,描绘的是一个宽容、仁爱的领导形象,包括7个条目,分别是:“当部属偶尔未能完成工作任务时,他会尽量从宽处理”“他会创造宽松的环境以便部属诉说不满”“部属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他会主动给予支持”“他会主动了解部属工作上的困难”“部属的生活遇到困难时,他会主动给予支持”“在布置工作任务时他会先征求部属意愿”和“他对部属的生活质量好坏非常关心”。第二维度是“情绪管理”,指的是领导对部属以及成员之间情绪状况的察觉、调节和管理能力,展现的是领导者的情绪智力水平以及互动过程中的主导能力,包括5个条目,分别是“他总能察觉团队成员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他擅长处理部属的负面情绪”“他总是能留意到部属情绪的变化”“他有能力调节部属间的冲突”和“与人交谈时他善于调动对方的积极性”。
3. 信度分析根据Hinkin(1998)的建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束后需要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一般学者认为,分量表的信度系数达到0.70以上就非常理想(Nunnally,1978),在0.60~0.70之间也可以接受(Peterson,1994;Slater,1995)。样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折半信度分析结果见表 1最后两行,较为理想。
4. 验证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束后两周,我们对12个条目重新编号后发放了第二次问卷。将回收的有效样本(N=166)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情感型领导的二维结构是否得到另外样本数据的支持。
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时,我们通过比较竞争模型的拟合情况来确定最佳模型。主要比较了三个竞争模型:(1)虚无模型,即12个条目不存在任何公因子;(2)单因素模型,即12个条目共享一个公因子;(3)二因素模型,即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将相应条目负荷在两个独立的因子上。经过调试,三个模型的最佳拟合情况如表 2所示。
| 模型 | χ2/df | RMR | RMSEA | GFI | AGFI | PGFI | NFI | CFI |
| 虚无模型 | 20.29 | 0.41 | 0.34 | 0.28 | 0.15 | 0.24 | 0.00 | 0.00 |
| 单因素模型 | 8.58 | 0.10 | 0.21 | 0.64 | 0.49 | 0.45 | 0.65 | 0.68 |
| 二因素模型 | 2.39 | 0.05 | 0.09 | 0.90 | 0.84 | 0.54 | 0.92 | 0.95 |
结果表明,二因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都优于其他模型。单就二因素模型来看:首先,绝对拟合指数χ2/df为2.39,小于3,均方根残差(RMR)小于0.05,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小于0.10,拟合优度指数(GFI)和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也都基本达到0.90的理想水平,表明模型可以接受;其次,相关指数(NFI=0.92,CFI=0.95)均大于0.90,较为理想;最后,简约拟合优度指数(PGFI)为0.54,大于0.50,表明模型是较为简约的。综上,拟合优度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说明该模型的结构是合理的。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因子载荷情况见图 1。可以看出,所有条目在相应潜变量上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在0.5~1.0之间,并且全部通过了t检验,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各条目的误差也都显著小于0.70。这说明本研究的各变量具有充分的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
| 图 1 情感型领导二维结构模型的完全标准化解 |
上述分析和研究表明:实证得出的情感型领导二维结构与预期的理论构念相一致;自编量表具有较好的表面效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聚合效度和一致性信度。
三、 研究二:情感型领导量表的区分效度和预测效度检验研究二通过比较情感型领导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的相关性,来检验所开发量表的区分效度;此外,通过探究情感型领导对部属的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影响来检验量表的预测效度,并通过检验情感型领导的增值效度来验证情感型领导对于这两个结果变量预测的重要作用。
(一) 情感型领导与离职倾向促使员工产生离职倾向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他们的情感状态以及他们在工作中的情绪体验。一方面,在工作和生活中,员工总会遇到一些靠自身力量难以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产生挫败感、无力感等消极情感,久而久之就会对工作产生不满和倦怠,形成较高的离职倾向(Wright和Cropanzano,1998;Kim和Stoner,2008)。此外,员工与团队成员尤其是与领导之间的情感关系对其离职倾向会有显著影响(Harris等,2009)。最近的研究还表明,生活中外部事件的负面影响也可能触发员工的离职行为(翁清雄等,2014)。另一方面,情绪渗透于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我们的认知、动机以及行为的关键心理驱动力(Kellett等,2002);离职倾向和离职行为被认为与情绪驱动有直接的联系(Wright和Cropanzano,1998)。有研究表明,员工的主动离职很多时候并不是经过认真分析的理性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释放、总被压抑着而做出的冲动决定(Côté和Morgan,2002),尤其是那些需要付出大量情绪劳动的员工,情绪衰竭和情绪紊乱对其离职倾向的影响尤为显著(Chau等,2009;Goodwin等,2011)。
很多研究表明领导对部属的关怀会让部属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支持和关爱,进而产生情感承诺(Wayne等,1997;Maertz Jr等,2007)。首先,来自组织特别是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能够帮助员工更好地克服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降低他们的挫败感和无助感,从而使他们对组织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愿意持续留在组织中(Kim和Stoner,2008)。其次,领导对部属个人需要的关心,对他们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尊重和支持也会提高其工作满意度,使其不愿意离开组织(Mobley,1977)。最后,领导在工作中对部属的支持行为(Peccei和Rosenthal,2001)和商议行为(Thomas和Velthouse,1990)能够有效提升部属的心理授权水平,让他们体验到较高的工作意义感(凌俐和陆昌勤,2007),进而对组织产生认同感,愿意持续留在组织中。从情绪角度来看,本文所研究的情感型领导具备较高的情绪智力,善于处理和应对部属情绪方面的问题,这就有助于部属在心理上认同领导、信任领导,与领导建立基于互相认同的心理契约,进而降低离职意愿(Kiel和Watson,2009)。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情感型领导(H1a情感关怀,H1b情绪管理)与部属的离职倾向负相关。
(二) 情感型领导与建言行为Wang等(2014)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发现,当个体对组织有较高的情感承诺时,他们会主动回报组织,积极的建言就是回报的方式之一。段锦云(2011)则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对领导的认同和信任会让员工感知到更多的心理安全,降低对建言风险的感知,进而产生更多积极的建言行为。汪林等人(2009)从领导—成员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与领导建立良好关系并从中获益的部属会因为对内部人身份的认知而产生较高的责任心,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为。而本文所研究的情感型领导,会通过对部属工作和福利的关心和支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关怀,增加部属对组织和领导的积极情感(Wayne等,1997;Vandenberghe等,2004)。领导对部属的关爱还体现在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关心上,比如在部属生病住院时去医院看望,出席部属家的婚丧嫁娶仪式等,从而提升部属对自己的信任(穆桂斌和孙健敏,2013)。同时情感型领导对部属的过错尽量从宽处理也会降低部属实施建言的心理防线(Caldwell和Dixon,2010)。所以,根据社会交换和社会认同等理论,我们预期情感型领导对部属的情感关怀与部属的建言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建言是指员工向组织或者领导提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建议,这对员工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傅强等,2012)。情绪的扩展与构建理论指出,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个人的思维活动序列,提高个体认知的灵活性,有利于个体更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Fredrickson,2001;Amabile等,2004)。也就是说,积极情绪状态对个体的认知过程有促进作用,能够提高个体产生有效建言的可能性。另外,当员工产生了建设性想法时,是否实施建言行为,还会受建言的安全性及效用的影响(Detert和Edmondson,2006)。风险决策相关研究指出,积极情绪的个体在决策时,对结果更加乐观,对自身的判断更加自信,更愿意冒险,而消极情绪的个体则比较悲观,不愿意承担风险,决策时更加保守(如,Lauriola和Levin,2001)。因此,处于积极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建议会被上司采纳,对可能给自身带来的不良后果评估较低,安全性与效用评估都比较高,因此更愿意实施建言行为。善于进行情绪管理的情感型领导能够有效调动部属的积极性,使他们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下,由此我们预期情绪管理与部属的建言行为也正相关。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情感型领导(H2a情感关怀,H2b情绪管理)与部属的建言行为正相关。
(三) 研究程序与方法 1. 测试对象为降低同源偏差,在上次问卷结束一周后我们向这166名参与者发放了新一轮问卷,请他们对近三个月的工作状态以及直接上司的领导行为进行评估,对于有效问卷的填写者,给予30元的现金奖励,共回收有效问卷143份。样本的分布情况如下:男性占70.6%;从年龄上看,25岁以下、26~30岁、31~40岁、41岁及以上者各占18.2%、39.9%、24.5%和17.5%;从职级上看,高层、中层、基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各占12.6%、23.8%、60.1%和3.5%;从学历上看,专科及以下、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者各占4.9%、55.9%和39.2%。
2. 测量工具采用Likert 5点法计分,1~5分分别表示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及非常符合。
(1)领导风格。采用Ogbonna和Harris(2000)编制的13条目量表,包括三个分量表。参与型领导包括“在做决定之前,我的上司总是会考虑我们大家的想法”等5个条目;工具型领导包括“工作上,我的上司决定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等4个条目;支持型领导包括“我的上司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能够更加愉快地工作”等4个条目。三个分量表的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6、0.78和0.78。
(2)离职倾向。采用Mobley和Horner(1978)编制的4条目量表,样题项包括“我基本上没有想过离开目前这个单位”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3)建言行为。采用LePine和Van Dyne(1998)编制的8条目量表,样题项包括“我会积极提出一些改善我们单位问题的建议”等。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0.91。
(4)控制变量。此外,以往研究的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收入水平以及职务层级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Arnold和Feldman,1982;Barak等,2001),因此,我们同时测量了这些变量,并在回归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3. 研究方法Hinkin(1995)指出可以通过比较量表测得结果与测量另外某个构念的其他量表测得结果的相关系数来检验自编量表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理论上相关的构念测量结果应该相近,也就是相关性较高,这可以表明量表具有聚合效度;理论上相异的构念测量结果应该差异较大,即相关性很低,表明量表具有区分效度(DeVellis,2012)。另外,验证性因素分析也可用于验证量表的区分效度。最后,我们将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情感型领导对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预测作用,通过分步回归法检验情感型领导对结果变量的增值效度,进一步验证情感型领导的有效性。
(四) 研究结果 1. 相关分析情感型领导及其二维度、参与型领导、工具型领导、支持型领导、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3所示。
| 均值 | 标准差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
| 1.性别a | 1.29 | 0.46 | - | |||||||||||
| 2.年龄b | 2.50 | 1.15 | -0.03 | - | ||||||||||
| 3.月收入c | 4.34 | 1.64 | -0.22** | 0.59** | - | |||||||||
| 4.职务层级d | 2.45 | 0.76 | 0.04 | 0.69** | 0.56** | - | ||||||||
| 5.情感关怀 | 3.21 | 0.74 | -0.06 | -0.08 | -0.07 | 0.08 | 0.89 | |||||||
| 6.情绪管理 | 3.21 | 0.77 | -0.12 | 0.01 | 0.02 | 0.08 | 0.58** | 0.88 | ||||||
| 7.情感型领导 | 3.21 | 0.67 | -0.10 | -0.05 | -0.03 | 0.09 | 0.92** | 0.85** | 0.91 | |||||
| 8.参与型领导 | 3.17 | 0.82 | -0.02 | -0.06 | -0.00 | 0.16 | 0.29** | 0.18* | 0.27** | 0.86 | ||||
| 9.工具型领导 | 3.16 | 0.74 | 0.04 | -0.18* | -0.19* | -0.09 | 0.21* | 0.12 | 0.19* | 0.42** | 0.78 | |||
| 10.支持型领导 | 2.85 | 0.76 | 0.02 | -0.15 | -0.12 | -0.07 | 0.46** | 0.32** | 0.45** | 0.61** | 0.43** | 0.78 | ||
| 11.离职倾向 | 2.28 | 0.94 | -0.10 | -0.13 | -0.13 | -0.13 | -0.24** | -0.37** | -0.33** | -0.17* | -0.04 | -0.23** | 0.87 | |
| 12.建言行为 | 3.51 | 0.70 | -0.29** | 0.25** | 0.23** | 0.29** | 0.22 | 0.28** | 0.28** | 0.18* | 0.05 | 0.14 | -0.04 | 0.91 |
| 注:*p<0.05,**p<0.01;a:1=男性,2=女性;b:1=25岁及以下,2=26~30岁,3=31~40岁,4=41岁及以上;c:1=3 000元及以下,2=3 001~5 000元,3=5 001~8 000元,4=8 000元以上;d:1=一线员工,2=基层管理者,3=中层管理者,4=高层管理者; | ||||||||||||||
从相关性数据来看,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分量表与支持型领导风格相关性最高(r=0.46,p<0.01;r=0.32,p<0.01),且都达到0.01的显著水平,与参与型领导风格相关性也比较高(r=0.29,p<0.01;r=0.18,p<0.05),与工具型领导风格的相关性最低(r=0.21,p<0.05;r=0.12,p=0.15)。情感型领导的分量表与参与型和支持型领导风格有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性,说明情感型领导量表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同时,情感型领导与工具型领导相关性较低,根据其内涵和定义上的区别,表明情感型领导量表与工具型领导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度。
从表 3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情感关怀与离职倾向负相关(r=-0.24,p<0.01),与建言行为正相关(r=0.22,p<0.05);情绪管理也与离职倾向负相关(r=-0.37,p<0.01),与建言行为正相关(r=0.28,p<0.01);情感型领导总分同样与离职倾向负相关(r=-0.33,p<0.01),与建言行为正相关(r=0.28,p<0.01)。而参与型领导和支持型领导虽然也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r=-0.17,p<0.05;r=-0.23,p<0.01),但显著程度不及情感型领导。同时可以看出,这三种领导风格,仅参与型领导与部属建言行为相关性显著(r=0.18,p<0.05),另外两种不显著。此外,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性别、年龄、月收入以及职务层级都与建言行为显著相关(r=-0.29,p<0.01;r=0.25,p<0.01;r=0.23,p<0.01;r=0.29,p<0.01)。
2. 区分效度分析根据前文的相关分析,我们将情感型领导(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之间相关度较高的概念进行配对,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区分度。结果如表 4所示,例如,M-双因素(AL1和PL)与M-单因素(AL1+PL)两行所对应的数据分别表示将情感关怀和参与型领导负荷在两个独立的因子上以及将二者合并共享一个因子时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的各拟合指数。可以看出,在每一组竞争模型中,三因素和双因素模型都优于单因素模型,同时AVE值都在0.5标准之上,且AVE值的平方根(0.71~0.80)都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46,见表 3),这些都证实了情感型领导量表的区分效度(Zhang等,2015),表明情感型领导(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是不同的概念。
| χ2/df | RMR | RMSEA | GFI | AGFI | NFI | CFI | AVES | ||
| M-双因素 | AL1和PL | 1.90 | 0.05 | 0.08 | 0.91 | 0.86 | 0.92 | 0.96 | AVEAL1=0.52 |
| M-单因素 | AL1+PL | 8.52 | 0.15 | 0.23 | 0.65 | 0.47 | 0.58 | 0.61 | AVEPL=0.60 |
| M-双因素 | AL1和SL | 1.77 | 0.05 | 0.07 | 0.93 | 0.87 | 0.92 | 0.96 | AVEAL1=0.52 |
| M-单因素 | AL1+SL | 6.04 | 0.11 | 0.19 | 0.75 | 0.62 | 0.68 | 0.72 | AVESL=0.50 |
| M-双因素 | AL2和PL | 1.69 | 0.04 | 0.07 | 0.94 | 0.89 | 0.94 | 0.98 | AVEAL2=0.63 |
| M-单因素 | AL2+PL | 7.43 | 0.16 | 0.21 | 0.83 | 0.69 | 0.73 | 0.76 | AVEPL=0.61 |
| M-双因素 | AL2和SL | 1.23 | 0.03 | 0.04 | 0.96 | 0.92 | 0.95 | 0.99 | AVEAL2=0.64 |
| M-单因素 | AL2+SL | 7.76 | 0.14 | 0.22 | 0.74 | 0.57 | 0.67 | 0.69 | AVESL=0.50 |
| M-三因素 | AL1、AL2和PL | 1.85 | 0.05 | 0.07 | 0.87 | 0.82 | 0.88 | 0.94 | AVEAL1=0.52 |
| M-单因素 | AL1+AL2+PL | 6.92 | 0.13 | 0.20 | 0.58 | 0.45 | 0.52 | 0.55 | AVEAL2=0.64 AVEPL=0.60 |
| M-三因素 | AL1、AL2和IL | 1.77 | 0.07 | 0.07 | 0.88 | 0.83 | 0.88 | 0.95 | AVEAL1=0.51 |
| M-单因素 | AL1+AL2+IL | 6.25 | 0.12 | 0.19 | 0.60 | 0.48 | 0.54 | 0.58 | AVEAL2=0.64 AVEIL=0.60 |
| M-三因素 | AL1、AL2和SL | 1.72 | 0.05 | 0.07 | 0.88 | 0.83 | 0.89 | 0.95 | AVEAL1=0.52 |
| M-单因素 | AL1+AL2+SL | 5.71 | 0.10 | 0.18 | 0.64 | 0.53 | 0.58 | 0.62 | AVEAL2=0.64 AVESL=0.50 |
| 注:AL1-情感关怀,AL2-情绪管理,PL-参与型领导,IL-工具型领导,SL-支持型领导。 | |||||||||
为检验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分别将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情感型领导两个维度对因变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我们采用分步回归分析方法。第一步是加入控制变量,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是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分别加入“情感关怀”“情绪管理”以及“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回归结果见表 5。
| 变量 | 离职倾向(β) | 建言行为(β) | ||||||
| 第一步 | 第二步 QG |
第三步 QX |
第四步 QG+QX |
第一步 | 第二步 QG |
第三步 QX |
第四步 QG+QX |
|
| 控制变量 | ||||||||
| 性别 | -0.13 | -0.16 | -0.18* | -0.18* | -0.31*** | -0.28** | -0.27** | -0.27** |
| 年龄 | -0.04 | -0.10 | -0.07 | -0.08 | 0.08 | 0.12 | 0.10 | 0.11 |
| 月收入 | -0.12 | -0.15 | -0.14 | -0.15 | -0.03 | -0.01 | -0.02 | -0.01 |
| 职位层级 | -0.03 | 0.05 | 0.04 | 0.05 | 0.27* | 0.21 | 0.23* | 0.21 |
| 情感型领导 | ||||||||
| 情感关怀 | -0.27*** | -0.07 | 0.19* | 0.08 | ||||
| 情绪管理 | -0.39*** | -0.35*** | 0.23** | 0.19* | ||||
| R2 | 0.04 | 0.11 | 0.19 | 0.19 | 0.18 | 0.21 | 0.23 | 0.24 |
| ∆R2 | 0.04 | 0.07*** | 0.15*** | 0.15*** | 0.18*** | 0.04* | 0.05** | 0.06** |
| F | 1.32 | 3.30 | 6.27 | 5.29 | 7.52 | 7.46 | 8.29 | 7.03 |
| ∆F | 1.32 | 10.84*** | 25.13*** | 12.76*** | 7.52*** | 6.09* | 9.51** | 5.14** |
| 注:*p<0.05;**p<0.01;***p<0.001。QG和QX分别表示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QG+QX表示同时加入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 | ||||||||
首先,检验情感型领导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以离职倾向为因变量,先后将情感型领导的两个维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最后将二者同时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情感关怀与情绪管理都对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7,p<0.001;β=-0.39,p<0.001),假设H1成立。
其次,检验情感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将建言行为作为因变量,先后将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作为自变量进行两次回归,第三次同时加入二者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都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9,p<0.05;β=0.23,p<0.01),假设H2成立。
最后,从表 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同时加入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时,情绪管理对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β=-0.35,p<0.001;β=0.19,p<0.05),但情感关怀对二者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β=-0.07,p=0.49;β=0.08,p=0.38)。
前文已经论述了情感型领导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是能够被区别开来的不同概念,而为了验证情感型领导在对员工的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预测作用方面的独特性和有效性,我们在对相关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控制的基础上,第二步加入参与型、工具型和支持型领导三者之一,最后再加入情感型领导,以检验其增值效度。分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
| 变量 | 离职倾向 | 建言行为 | ||
| β | ∆R2 | β | ∆R2 | |
| M1-1参与型领导 | -0.17* | 0.03* | 0.13 | 0.02 |
| M1-2参与型领导+情感型领导 | -0.34*** | 0.11*** | 0.22** | 0.04** |
| M2-1工具型领导 | 0.01 | 0.00 | 0.10 | 0.01 |
| M2-2工具型领导+情感型领导 | -0.38*** | 0.13*** | 0.23** | 0.05** |
| M3-1支持型领导 | -0.25** | 0.06** | 0.17* | 0.03* |
| M3-2支持型领导+情感型领导 | -0.31*** | 0.08*** | 0.20* | 0.03* |
| 注:*p<0.05;**p<0.01;***p<0.001。表中数值表示最后加入的自变量对应的β和∆R2,如“M1-2参与型领导+情感型领导”一行的数值表示在M1-1方程的基础上加入“情感型领导”后,“情感型领导”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 ||||
模型M1-1、M2-1和M3-1分别显示了参与型、工具型和支持型领导对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参与型领导和支持型领导对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7,p<0.05;β=-0.25,p<0.01),支持型领导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7,p<0.05),而工具型领导对这两个因变量都没有显著作用。
从模型M1-2、M2-2和M3-2来看,在分别控制了参与型、工具型以及支持型领导后,情感型领导对离职倾向(∆R2=0.11,p<0.001;∆R2=0.13,p<0.001;∆R2=0.08,p<0.001)和建言行为(∆R2=0.04,p<0.01;∆R2=0.05,p<0.01;∆R2=0.03,p<0.05)的增值效度都很显著。
四、 讨论与结论本研究构建和分析了情感型领导的二维结构,包括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两个维度,开发了一套包含12个条目的情感型领导量表,并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其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相关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情感型领导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能够有效区分开来。回归分析结果证实情感型领导与员工的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与员工的建言行为显著正相关;同时,在分别控制了参与型、工具型以及支持型领导的基础上,再加入情感型领导,显示情感型领导对结果变量的增值效度显著,进一步暗示相比于其他三种领导行为,情感型领导可以额外解释员工的关键行为和态度(即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方差。
(一) 理论贡献 1. 基于儒家“五常”理论,界定了情感型领导的概念内涵,揭示了情感型领导的二维结构,并开发了相应的量表本研究基于儒家“五常”理论,将情感型领导定义为一种特别重视组织中人际关系和情感氛围的人性化领导风格,它包含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两方面内容。情感关怀是指领导者以沟通协商的方式开展工作,主动关心部属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满足员工情感上的需要。情绪管理反映情感型领导能准确识别自己和部属的情绪状态以及成员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并善于对部属的情绪以及部属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
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了情感型领导的二维结构,开发了情感型领导量表,并通过信度效度检验对量表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最终形成的二维度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首先,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抽取出2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72.92%,表明情感型领导这一概念存在明显的二维结构。根据对应条目的内容,本研究将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其次,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高于0.70,说明分量表各题项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再者,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构念,分别反映了情感型领导行为的不同方面。第四,与概念上相关的变量(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做相关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自编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表明情感型领导区别于这些概念。最后,将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作为结果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检验情感型领导的预测效度,结果显示情感型领导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与建言行为显著正相关,且情感型领导具有较好的增值效度,表明自编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情感型领导概念的界定和量表的开发为后续定量分析情感型领导的影响因素以及情感型领导和团队绩效、员工态度或行为的关系打下了基础,丰富了领导风格相关研究。
2. 检验了情感型领导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之间的区别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情感型领导与参与型领导、支持型领导之间的相关程度要大于与工具型领导之间的相关程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情感型领导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即情感型领导及其两个维度均区别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此外,从这四种领导风格与离职倾向、建言行为相关系数的比较来看,情感型领导与离职倾向的相关性要高于另外三种领导风格与离职倾向的相关性。同时,情感型领导与部属的建言行为也显著相关,而另外三种领导风格,仅参与型领导与部属的建言行为显著相关。最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分别控制了参与型、工具型和支持型领导后,情感型领导均能额外解释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方差。可见,相比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情感型领导与部属的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之间具有更强的关联性。综上所述,本研究分析了四种领导风格之间的关系,讨论了不同领导风格在领导效能上的差异,从而丰富了领导风格和领导有效性相关研究。
3. 验证了情感型领导与员工离职倾向及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情感型领导的两个维度对员工离职倾向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刘平青等(2014)在对领导风格、员工关系以及员工离职倾向的研究中发现,领导对部属的关心和帮助能够有效降低部属的离职倾向,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鉴于组织承诺可以显著影响离职倾向(叶仁荪等,2005),笔者推测,领导的情感关怀可能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承诺而影响其离职倾向。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还发现除了领导对部属的关怀和照顾之外,领导在情绪管理方面的努力也有助于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这些研究发现进一步检验了情感型领导的有效性,也拓展了关于离职倾向前因变量的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情感型领导的两个维度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Saunders等(1992)认为如果领导者平易近人,能够与部属进行积极的互动和反馈,那么部属建言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与本研究的发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因为,领导的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行为可以拉近领导与部属的距离,创造开放轻松、畅所欲言的氛围。不过情感型领导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对企业发展有利的建议才对部属展示开放性,他们更多地是出于对部属内心真实感受的重视。
从增值效度的检验结果来看,情感关怀对情绪管理与离职倾向之间关系的增值效度并不显著,说明员工离职倾向的产生更多的是出于情绪方面的问题,而不是领导在情感关怀方面的努力不够。这可能是由于,随着“80后”“90后”成为职场主力,这些新生代员工因为成长环境和背景的差异,形成了与以往员工存在巨大差异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给组织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包括离职问题(伍晓奕,2007;路冬英和李菁,2014)。学者们(如,杨富云,2011)发现,新生代员工与“80前”员工相比,自尊心更强、更敏感、受挫能力更低,而情绪调节能力又相对较差,这些是造成他们频繁离职的主要原因。
同样地,情感关怀对情绪管理与建言行为之间关系的增值效度也不显著,说明员工的建言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受情绪管理的影响,而领导者的情感关怀在此基础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建言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冒险行为,是对权威的挑战(Detert和Burris,2007),因此员工即使与领导有较好的关系,也不一定愿意去表达自己对组织的建议。领导者的情绪管理能够提高员工的积极情绪,这种积极情绪不仅有助于员工产生更多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点子,也能降低员工对建言风险的感知,从而能够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
(二) 研究启示基于本研究的结论,我们在管理者行为方式以及对领导者的选择和培养等方面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领导者可以通过遵循情感型领导的行为风格来拉近与部属的距离,与部属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营造和谐、积极的团队或组织氛围。一方面,领导者可以通过情感上的关怀获取部属对领导的认同,即领导者需关注部属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疑惑,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难题,以沟通协商的方式与部属共事;另一方面,领导者可以通过情绪管理使部属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即领导者需关注部属的情绪状态以及成员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主动调节部属情绪和成员间关系,与部属沟通时要注意对部属积极性的调动。组织在培训各级管理者时,也要注重提升管理者的情感关怀和情绪智力水平。
第二,管理者可以通过采用情感型领导行为来降低组织的离职率。在这个“跳槽”频发的年代,员工面临的外部“诱惑”越来越多,职业转换也变得越来越容易,而高离职率对于组织来说却是巨大的沉没成本。要想为组织留住人才,尤其是核心人才,领导者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很关键。情感型领导可以通过与部属之间情感关系的建立来提升部属对自己的信任和追随,进而降低他们的离职倾向。
第三,管理者可以通过采用情感型领导行为来达到激励员工建言的效果。随着外部环境复杂性、动态性的提高,对于领导者来说,仅凭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识别和应对组织面临的挑战变得越来越困难,员工在应对和处理关键问题和事件上的看法和建议对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段锦云,2011)。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情感型领导对部属的情感关怀和情绪管理能够有效激励他们为组织的发展建言献策,其中情绪管理(促进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尤为明显。
(三)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虽然本研究遵循了较为严格的程序和标准,但仍然难免存在一些局限。
第一,本研究试图通过多次问卷调查来减少可能产生的同源偏差问题,但是数据采集均采用自我报告形式,仍然可能造成共同方法偏误(Podsakoff等,2003)。对于领导行为的评价,本研究所采用的部属打分评价是较为客观和准确的一种方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通过上级评价来观测员工的建言行为。
第二,本研究探讨了情感型领导对员工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这两个结果变量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研究其对其他重要结果变量的作用,包括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等。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不同样本的收集,探究情感型领导对其他重要组织结果的影响,以便进一步明晰情感型领导的作用。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察不同情境下情感型领导有效性的差异,或者探讨情感型领导与其他领导类型的结合是否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此外,情感型领导的前因变量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第三,本研究探讨了情感型领导与参与型、工具型及支持型领导的关系,证实这几个概念是能够进行有效区分的,并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情感型领导对离职倾向和建言行为的显著增值效度。不过,在领导内涵和具体行为方面,与情感型领导更类似的是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本文没有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存在失误。虽然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未来仍然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二者的共性和差异。
第四,领导是一种镶嵌在文化背景下的特定行为,文化存在差异,领导的内涵与效能就可能存在差异(Hofstede,1980)。情感型领导是基于中国的情境发展出来的构念,它主要反映中国文化、社会情境和组织经验对有效领导行为的理解,体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观”(李垣等,2008;席酉民和韩巍,2010)。而在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其他东亚国家,情感型领导的有效性很可能也可以得到验证。不过,这种领导行为是否能够比西方经典的领导行为构念更好地预测中国企业组织的管理绩效,以及这种领导行为对其他文化背景下组织的结果变量能否有较好的预测作用,都有待后续研究继续进行探索和检验。
| [1] | 陈永霞, 贾良定, 李超平, 等. 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与员工的组织承诺:中国情景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1) : 96–105. |
| [2] | 成中英, 晁罡, 申传泉, 等. 美德的有效领导:基于儒家视角的政治领导力分析[J].管理学报,2014(11) : 1601–1604. |
| [3] | 厉凌, 陈同扬. 中国情境下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离职意图的影响分析[J].商业时代,2010(23) : 91–93. |
| [4] | 刘小华. 试论儒家伦理思想与企业经营管理[J].中国软科学,1996(4) : 95–99. |
| [5] | 路冬英, 李菁. 企业90后员工"闪辞"问题探析[J].经营管理者,2014(24) : 145–146. |
| [6] | 王椿阳, 夏春, 朱永新. "以和为贵"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创建和谐型组织[J].管理现代化,2006(6) : 19–21. |
| [7] | 翁清雄, 陈银龄, 席酉民. 员工离职决策多路径模型案例分析-基于离职倾向与外在事件的两维视角[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9) : 48–58. |
| [8] | 席酉民, 韩巍. 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 32–40. |
| [9] | 郑伯埙, 周丽芳, 樊景立. 家长式领导量表:三元模式的建构与测量[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0(14) : 3–64. |
| [10] | Arnold H J, Feldman D C.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job turnover[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2,67(3) : 350–360. |
| [11] | Ashkanasy N M, Tse B.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s management of emotion:A conceptual review[A]. Ashkanasy N, Hartel C, Zerbe W(Eds.). Emotions in the workplace: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C]. Westport, Connecticut:Quorom Books, 2000:221-235. |
| [12] | Avolio B J, Bass B M, Jung D I. Re-examining the components of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using the multifactor leadership[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999,72(4) : 441–462. |
| [13] | Babbie 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M].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2012 . |
| [14] | Barbuto Jr J E, Wheeler D W. Scal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clarification of servant leadership[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6,31(3) : 300–326. |
| [15] | Chau S L, Dahling J J, Levy P E, et al. A predictive study of emotional labor and turnover[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9,30(8) : 1151–1163. |
| [16] | Côté S, Morgan L M.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job satisfaction, and intentions to quit[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2,23(8) : 947–962. |
| [17] | Derue D S, Nahrgang J D, Wellman N E D, et al. Trait and behavior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An integration and meta-analytic test of their relative validity[J].Personnel Psychology,2011,64(1) : 7–52. |
| [18] | Detert J R, Burris E R.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employee voice:Is the door really ope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4) : 869–884. |
| [19] | DeVellis R F. Scale development:Theory and application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2 . |
| [20] | Gao L P, Janssen O, Shi K. Leader trust and employee voi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owering leader behavior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1,22(4) : 787–798. |
| [21] | Goleman D, Boyatzis R, McKee A. Primal leadership:The hidden driver of great performanc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1,79(11) : 42–51. |
| [22] | Goodwin R E, Groth M, Frenkel S J.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al labor, job performance, and turnover[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11,79(2) : 538–548. |
| [23] | Hinkin T R. A brief tutori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for use in survey questionnaires[J].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1998,1(1) : 104–121. |
| [24] | Hinkin T R. A review of scale development practices i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5,21(5) : 967–988. |
| [25] | Kellett J B, Humphrey R H, Sleeth R G. Empathy and complex task performance:Two routes to leadership[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2,13(5) : 523–544. |
| [26] | Kim H, Stoner M. Burnou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social workers:Effects of role stress, job autonomy and social support[J].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2008,32(3) : 5–25. |
| [27] | Kumar Mishra S, Bhatnagar D. Linking emotional dissonance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o turnover intention and emotional well-being:A study of medical representatives in India[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0,49(3) : 401–419. |
| [28] | LePine J A, Van Dyne L. Predicting voice behavior in work group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8,83(6) : 853–868. |
| [29] | Maertz Jr C P, Griffeth R W, Campbell N S, et al.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 on employee turnover[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7,28(8) : 1059–1075. |
| [30] | Mobley W H. Intermediate linka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employee turnover[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77,62(2) : 237–240. |
| [31] | Mobley W H, Horner S O, Hollingsworth A T. An evaluation of precursors of hospital employee turnover[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78,63(4) : 408–414. |
| [32] | Morrison E W. Employee voice behavior:Integration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1,5(1) : 373–412. |
| [33] | Newman M A, Guy M E, Mastracci S H. Beyond cognition:Affective leadership and emotional labor[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9,69(1) : 6–20. |
| [34] | Ogbonna E, Harris L C. Leadership styl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K companies[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0,11(4) : 766–788. |
| [35] | Saunders D M, Sheppard B H, Knight V, et al. Employee voice to supervisors[J].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1992,5(3) : 241–259. |
| [36] | Tse H H M, Huang X, Lam W. Why do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matter for employee turnover? A multi-foci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3,24(5) : 763–776. |
| [37] | Vandenberghe C, Bentein K, Stinglhamber F. Affec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supervisor, and work group:Antecedents and outcomes[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4,64(1) : 47–71. |
| [38] | Wang Q, Weng Q X, McElroy J C, et al. Organizational career growth and subsequent voice behavior:The role of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gender[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14,84(3) : 431–441. |
| [39] | Wright T A, Cropanzano R. Emotional exhaustion as a predictor of job performance and voluntary turnover[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8,83(3) : 486–493. |
| [40] | Zhang Y, Waldman D A, Han Y L, et al. 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s in people management: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2) : 538–566. |
 2016, Vol. 38
2016, Vol. 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