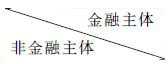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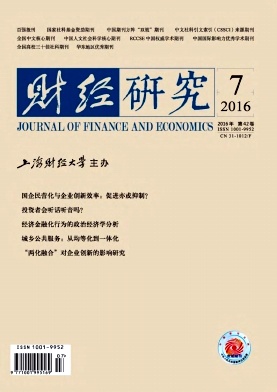 | 财经研究 2016年42卷第7期 |
- 鲁春义, 丁晓钦.
- Lu Chunyi, Ding Xiaoqin.
- 经济金融化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演化博弈框架
- 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Economic Financialization Behavior: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 财经研究, 2016, 42(7): 52-62,74
-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6, 42(7): 52-62,74.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6-03-01
2.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3.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2.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0世纪中后叶,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从以往通过政府权力投入货币流量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模式,转变为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市场来创造货币流量支撑扩大再生产。于是,资本家热衷于通过创造金融产品以分割剩余价值,而不再通过生产商品、创造剩余价值来获得利润,从而出现了金融繁荣与生产萎缩的经济状况,最终导致了2008年蔓延多国的金融危机。然而,有关经济金融化的本质、影响乃至生成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争议,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颇有不同。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金融化主要是指利用金融技术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将实体资产置换为金融资产的过程(Blackburn,2006;Langley,2013);而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化是指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支配,反映了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如股东权益在公司治理中地位不断上升(lazonick和O’Sullivan,2000;Roberts,2006)以及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的地位不断提高(Epstein,2005)。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金融化理论主要关注宏观金融层面,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关键(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 Galbis,1977;Mathieson,1980; Hellmann等,2001);而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化理论主要关注生产分配领域,分析发达国家的金融繁荣所导致的生产萎缩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Roberts,2006;Callinicos,2010),大多是对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批判(Sweezy,1995,1997;Lazonick,2012;González 和 Sala,2013)。本质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金融化理论植根于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之中,主要是从纯技术的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波动,但这种宏观模型无法分析各不同层次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强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与分配关系。但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金融化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缺乏从微观行为到宏观影响的机制分析。
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金融化的本质及其特征,指出金融化的本质在于资本积累演变为资本脱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交换而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增殖的过程,金融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公司治理目标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利润来源渠道的金融主导化、金融体系自由化及其业务全面证券化、食利阶层经济力量权力化;其次,从行为选择的角度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从而实现经济分析中微观基础与宏观总体的统一;最后,运用该模型系统而全面地分析经济主体对现实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研究发现:现实中家庭的金融行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以及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选择引起了这些群体间的动态经济关系转变,即非金融企业主要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而且试图摆脱银行等金融企业的融资束缚,金融企业则关注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并将普通家庭纳入其体系使之成为新的利润源泉,而普通家庭则被动金融化并被迫接受强势经济主体的二次剥削。这些动态经济关系的转变与经济主体的分利技术密切相关:在既定假设下,当非金融主体只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既可以促使一国经济走向新的稳定状态也可促使其走向崩溃;当非金融主体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和分利技术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经济可以实现演化稳定状态;如果改变既定假设,那么经济发展状态呈现崩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增加。模型中所展示的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表明,没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必然因非金融企业或金融企业的霸权而陷入危机。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揭示经济金融化的本质与特征;(2) 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主体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来解释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与经济发展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有利于我们从经济主体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危机的形成机制。
二、 金融化的产生、特征和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专门研究不确定性,因此也就没有涉及风险问题。但是,《资本论》中有关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的论述却蕴含了不确定性思想,而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这就为金融系统的生成创造了空间。事实上,伴随着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的进步以及劳动者数量和素质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效率和规模都大幅度提高了,而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只有在剩余价值实现之后才能进行。但在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存在很大风险,资本家要售出商品后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即使商品售出去并获得了交换价值,但只有把这些用货币衡量的交换价值进行投资后才能实现资本积累。历史经验表明,金融系统是市场经济中保证剩余价值实现的有效机制。
当金融发展到不再为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服务时,其运行方式将带来新的甚至更高的风险。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在金融系统中循环以分割剩余价值的现象就是金融化。它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公司治理中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导向呈现支配地位;二是资本获得利润的渠道逐渐从商品生产或贸易转移到了金融活动;三是资本市场规模及其作用越来越超过原有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四是社会中专门食利的阶层拥有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力量。那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为何会呈现这样的特征呢?
金融化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与拓展。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出现经济滞涨、新经济泡沫等现象。以全球化为代表的“空间修复”模式和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修复”模式,都难以缓解不断激化的资本积累矛盾,而以金融化为代表的“时间与空间修复”模式脱离了剩余价值生产领域以追求高额利润率而成为资本修复的新模式。显然,这种金融化模式的本质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马克思指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笫101页。 ①(①Hunt(1979)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以利息、利润和地租的形式给予资本家剥削的权力。”)②(②引自Hunt E X: Marx as a social economist: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Review of Social Economy,1979,37(3): 275-294.)那么,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之一,其本质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这种资本的价值增殖独立于生产过程,独立于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独立于新价值创造。因此,金融化的本质在于资本积累变成了资本脱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交换而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增殖的过程,且这个过程通过经济主体间的金融关系表现出来。从微观来看,金融化反映了经济主体从生产行为向非生产行为变化的过程,即非金融企业主要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而且试图摆脱银行等金融企业的融资束缚,金融企业则关注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并将普通家庭纳入其体系使之成为新的利润源泉,而普通家庭则被动金融化并被迫接受强势经济主体的二次剥削;从宏观来看,金融化反映了经济生产与分配方式的转变。
三、 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特征与演化博弈设定 (一) 经济主体金融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既然金融化反映了经济主体从生产行为向非生产行为变化的过程,那么从行为选择的角度来分析金融化问题,实现微观基础与宏观总体的统一,才能更系统而全面地理解其对现实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不同,真实世界的经济主体具有现实主义、整体主义和有限理性等特征。因此,对当前社会经济的金融化现象的分析,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是要注意对其历史背景和当前所处环境特点的分析;其二是要充分运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金融化问题,如不能把经济主体都视为同质性的;其三是分析金融化问题时也必须指出经济主体行为特点是过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正是这种有限理性容易引起经济危机。
由于演化博弈理论修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个人的完全理性假设,分析有限理性状态下个体与群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因此,可以引入含有上述特征的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金融化现象及其影响。
(二) 演化博弈在金融化分析中的框架设定现实中,专门从事金融活动的经济主体擅长于分割价值,可以称之为金融主体;另外一部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经济主体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统称为非金融主体。金融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影响着非金融主体的经济活动,而非金融主体的经济活动对这个社会经济系统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具体来看,前者包括金融机构等金融企业,后者包括非金融企业以及普通家庭。
由于金融主体与非金融主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两者行为关系自然表现出演化博弈中的非对称博弈关系。演化博弈与有限理性行为的结合之处在于博弈参与者的某个策略类型所占其群体比例的动态变化,尤其是该动态变化的速度是首要关注的变量。如果博弈参与者采取第一种策略,其行为的动态变化速度可描述为:
| $dx/dt=x({{u}_{1}}-\bar{u})=x\left( 1-x \right)(\text{ }{{u}_{1}}-\text{ }{{u}_{2}})$ | (1) |
可以把上述方程简记为F(x)=dx/dt,从而可以用该式讨论参与者行为的演化稳定策略。只需令F(x)=0,即可求出所有的参与者模仿的动态稳定状态,然后分析上述稳定状态的领域稳定性,从而得出演化稳定策略(ESS)。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重点分析非金融主体与金融主体之间的非对称博弈关系及其产生的金融市场影响以及宏观经济影响。其中,分别以局部稳定性和系统稳定性衡量金融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方向,同时以实现这些稳定性的条件来分析这些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
四、 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演化博弈过程及其经济关系 (一) 基本假设与模型的建立为了分析经济主体间金融化行为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及其可能实现的稳定社会经济状态,在此进行如下假设:
1. 经济中有两类经济主体(非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非金融主体可选择的策略为(参与投机,专注生产),金融主体可选择的策略为(从事投机,支持生产)。投机行为是对生产行为的一种分利,即分割生产的剩余价值。
2. 在给定的经济环境中,非金融主体参与投机但并不会转变为金融主体,金融主体可支持生产但并不会转变为非金融主体。
3. 双方的策略过程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进行,且每个主体可根据其他成员的策略选择考虑其在自身群体中的相对适应性来选择和调整各自的策略。
4. 参与投机的非金融主体占比为x,则专注于生产的非金融主体比重为1-x,定义大量非金融主体专注生产的社会为生产型社会,反之为投机型社会;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主体的比重为y,而支持生产的金融主体的比重为1-y。
本文用经济主体在其进行生产或金融化分利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作为其博弈决策的标准,可得到如下博弈收益矩阵(如表 1):
其中,α和β分别表示部分经济主体和全部经济主体从事生产活动时的社会财富增长率,θ1与θ2分别表示非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f为经济主体用于保护生产的资源比例(鲁春义,2015),A社会的初始总禀赋,R为金融主体的正常收益(生产贷款利息收入)。当非金融主体与金融主体都进行金融化分利时,其获得的新收益取决于各自的分利技术θ1与θ2,因此其收益分别为Aθ1与Aθ2;当非金融主体专注生产,而金融主体从事金融化分利活动时,金融主体的收益来源于生产中获得的收益(αA(θ2-f)),该部分取决于增加的产出(αA)、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以及非金融主体用于保护其资源的投入(f),剩余部分则为非金融主体所得([αA-αA(θ2-f)]);当非金融主体只进行金融化分利而金融主体只支持生产时,非金融主体获利为Aθ1,金融主体获取其正常收入(R);当非金融主体专注生产而金融主体也专注生产时,其收益分别与生产率成正比,分别为βA和βR。由于α、β、A和R等参数为外生决定,经济主体无法控制,因此视为既定参数,且R <A。
首先,推导非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方程。非金融主体的金融化分利所增加的收益为:
| ${{U}_{11}}=yA{{\theta }_{1}}+\left( 1-y \right)A{{\theta }_{1}}$ | (2) |
非金融主体的生产行为所增加的收益为:
| ${{U}_{12}}=y\alpha A(1-{{\theta }_{2}}+f)+\left( 1-y \right)\text{ }\beta A$ | (3) |
则非金融主体的预期平均收益为:
| ${{U}_{1}}=x{{U}_{11}}+\left( 1-x \right){{U}_{12}}$ | (4) |
因此,非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 $\begin{align} &F\left( X \right)=dx/dt=x({{U}_{11}}-\text{ }{{U}_{1}})=x\left( 1-x \right)({{U}_{11}}-\text{ }{{U}_{12}}) \\ &=Ax\left( 1-x \right)\{(\text{ }{{\theta }_{1}}+\beta )-y[\alpha \text{ }(1-\text{ }{{\theta }_{2}}+f)+\text{ }\beta]\} \\ \end{align}$ | (5) |
接下来,推导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的动态复制方程。金融主体从事分利行为所增加的收益为:
| ${{U}_{21}}=xA{{\theta }_{2}}+\left( 1-x \right)\alpha A({{\theta }_{2}}-f)$ | (6) |
金融主体支持生产行为所增加的收益为:
| ${{U}_{22}}=xR+\left( 1-x \right)\beta R$ | (7) |
则金融主体的预期平均收益为:
| ${{U}_{2}}=y{{U}_{21}}+\left( 1-y \right){{U}_{22}}$ | (8) |
因此,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 $\begin{align} &F\left( y \right)=dy/dt=y({{U}_{21}}-\text{ }{{U}_{2}})=y\left( 1-y \right)({{U}_{21}}-\text{ }{{U}_{22}}) \\ &=y\left( 1-y \right)\{x[{{\theta }_{2}}A-R+\text{ }\beta R-\text{ }\alpha A(\text{ }{{\theta }_{2}}-f)\left] - \right[\beta R-\alpha A(\text{ }{{\theta }_{2}}-f)]\} \\ \end{align}$ | (9) |
1.非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演化稳定分析。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理论,F(x)=0时可以解得有可能出现的平衡点,即x*=0(非金融主体都专注生产)和x*=1(非金融主体都参与投机)是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非金融主体的演化行为选择取决于y,其中y*为分界点,且y*=(θ1+β)/[α(1-θ2+f)+β]。令μ=α(1-θ2+f),则y*=(θ1+β)/(μ+β)=1-(μ-θ1)/(μ+β)。下面根据几个极端点分析非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演化动态。
首先,当y=(θ1+β)/(μ+β)时,总有F(x)=0,即当金融主体中完全从事金融化活动的比重为(θ1+β)/(μ+β)时,非金融主体选择参与金融化活动或生产活动所增加的收益是一样的。此时,无论非金融主体中从事金融化活动的比重(x)是多少,金融主体和非金融主体都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和谐关系,但这个稳定状态的位置由非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1)、生产收益率(μ)以及社会财富生产率(β)决定。当θ1>μ时,意味着分利技术带来的高收益超过生产行为,经济中从事投机行为的金融主体增加;当μ>θ1时,意味着分利技术带来的收益低于生产行为,经济中从事投机行为的金融主体减少。
其次,当y <(θ1+β)/(μ+β)时,F(0)′>0,F(1)′ <0,所以x=1为非金融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此式表明,当非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1)提高到一定程度或者生产收益率(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将导致y <y*,即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主体比重低于稳定临界点。此时,如果要向稳定状态发展,那么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主体会参与金融化活动,直至所有非金融主体参与投机性的金融化活动(当x=1时)。
最后,当y>(θ1+β)/(μ+β)时,F(0)′ <0,F(1)′>0,所以x=0为非金融主体演化稳定策略。此式表明,当非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1)降低到一定程度或者生产收益率(μ)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将导致y>y*,即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主体比重高于稳定临界点。此时,如果要向稳定状态发展,那么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主体将从事生产性活动,直至所有非金融主体都从事生产性活动(当x=0时)。
2.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演化稳定分析。同样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理论,F(y)=0时可以解得有可能出现的平衡点,即y*=0(金融主体都支持生产)和y*=1(金融主体都从事投机活动)是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金融主体的演化行为选择取决于x,其中x*为分界点,且x*=[βR-αA(θ2-f)]/[Aθ2-R+βR-αA(θ2-f)]。令ω=βR-αA(θ2-f),则x*=ω/[ω-(R-Aθ2)]。
首先,当x=ω/[ω-(R-Aθ2)]时,F(y)始终为零,即当非金融主体从事投机行为的比重为ω/[ω-(R-Aθ2)]时,金融主体选择参与金融化活动或支持生产活动所增加的收益是一样的。此时,无论金融主体中从事金融化活动的比重(y)是多少,金融主体和非金融主体都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和谐关系,但这个稳定状态的位置是由金融主体专注生产的收益与金融主体进行金融化所分利益之差决定的。
其次,当x>ω/[ω-(R-Aθ2)]时,F(0)′>0,F(1)′ <0,所以y=1为金融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此式表明,当金融主体在生产型社会中的比较利差下降或者在投机型社会中的比较利差上升时,将导致x>x*,即从事投机活动的非金融主体比重高于稳定临界点。此时,如果要向稳定状态发展,那么越来越多的金融主体会参与金融化活动,直至所有金融主体参与投机性的金融化活动(当y=1时)。
最后,当x <ω/[ω-(R-Aθ2)]时,F(0)′ <0,F(1)′>0,所以y=0为金融主体演化稳定策略。此式表明,当金融主体在生产型社会中的比较利差上升或者在投机型社会中的比较利差下降时,将导致x <x*,即从事投机活动的非金融主体比重低于稳定临界点。此时,如果要向稳定状态发展,那么越来越多的金融主体将专注于服务生产性经济活动,直至所有金融主体都专注于服务生产性经济活动(当y=0时)。这说明当大多数非金融主体都在从事生产活动时,金融主体将通过支持非金融主体的生产活动获得较高收益,此时可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状态。
(三) 经济主体金融化行为动态复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根据上述分析,金融化行为动态复制系统可表示为:
| $dx/dt=\text{ }Ax\left( 1-x \right)\{(\text{ }{{\theta }_{1}}+\beta )-y[\alpha \text{ }(1-\text{ }{{\theta }_{2}}+f)+\text{ }\beta]\}$ | (10) |
| $dy/dt=\text{ }y\left( 1-y \right)\{x[{{\theta }_{2}}A-R+\text{ }\beta R-\text{ }\alpha A(\text{ }{{\theta }_{2}}-f)\left] - \right[\beta R-\alpha A(\text{ }{{\theta }_{2}}-f)]\}$ | (11) |
在此系统中讨论演化稳定策略时,令F(x)=0和F(y)=0,可以解出有五个平衡点,分别为E1(0,0)、E2(0,1)、E3(1,0)、E4(1,1)和E5([βR-αA(θ2-f)]/[θ2A-R+βR-αA(θ2-f)],(θ1+β)/[α(1-θ2+f)+β])。由演化博弈理论可知,演化均衡指的是动态复制系统的平衡点对应的策略组合。由微分方程稳定定理可知,通过建立雅可比矩阵进行局部稳定分析可得出结果。设矩阵J为动态复制系统的雅可比矩阵:
| $\eqalign{ &J = \left| {{{\partial F\left( x \right)} \over {\partial x}}{{\partial F\left( x \right)} \over {\partial y}}{{\partial F\left( y \right)} \over {\partial y}}{{\partial F\left( y \right)} \over {\partial x}}} \right| = \cr &\left| \matrix{ A\left( {1 - 2x} \right)({\theta _1} + \beta ) - y\alpha (1 - {\theta _2} + f) + \left. \beta \right\} - Ax\left( {1 - x} \right)\left[ {\alpha (1 - {\theta _2} + f) + \beta } \right] \hfill \cr y\left( {1 - y} \right)\left[ {{\theta _2}A - R + \beta R - \alpha A({\theta _2} - f)} \right]\left( {1 - 2y} \right)x({\theta _2}A - R) - \left( {1 - x} \right)\left. {\left[ {\beta R - \alpha A({\theta _2} - f)} \right]} \right\} \hfill \cr} \right| \cr} $ |
那么,行列式的值和迹分别表示为:
| $Det\left( J \right)=\left[\partial F\left( x \right)/\partial x \right]\left[\partial F\left( y \right)/\partial y \right]-\left[\partial F\left( x \right)/\partial y \right]\left[\partial F\left( y \right)/\partial x \right]$ | (12) |
| $Tr\left( J \right)=\partial F\left( x \right)/\partial x+\partial F\left( y \right)/\partial y$ | (13) |
在局部稳定状态分析中,非金融主体金融化行为与其分利技术(θ1)、生产收益率(μ)以及社会财富生产率(β)密切相关,而金融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与由其分利技术(θ2)、非金融主体资源保护率(f)以及社会财富生产率(α)等所决定的比较利差密切相关。通过雅可比矩阵,可将各局部稳定状态进行对比,从而得到系统性稳定状态。经计算可知,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变化直接影响其他各经济变量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的动态变化以及稳定状态的位移。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在不同范围变动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经济状态,其变动范围有4个区间:区间1为(0,M+αf/(1-α)),区间2为(M +αf/(1-α),N+f),区间3为(N+f,(α-θ1)/α+f),区间4为((α-θ1)/α+f,1),其中,M=R(1-β)/[A(1-α)],N=βR/(αA),而α、β、A和R等参数为外生决定。那么,这4个区间分别由非金融主体用于保护其资源的投入(f)和非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1)所内生决定。如果将非金融主体行为表示为Φ=φ(f,θ1),那么经济状态区间可以加以简化:区间1为(0,Φ1),区间2为(Φ1,Φ2),区间3为(Φ2,Φ3),区间4为(Φ3,1)。其中,Φ1=φ1(f,0)=M+αf/(1-α),表示非金融主体行为由其用于保护资源的投入(f)决定,同时以社会财富增长率(反映社会生产率)衡量的系数变动αf/(1-α)能增强或削弱f的影响程度;Φ2=φ2(f,0)=N+f,表示非金融主体行为由其用于保护资源的投入(f)决定,其系数为常数1,即社会财富增长率对f的强度和方向都没有影响;Φ3=φ3(f,θ1)=(α-θ1)/α+f,表示非金融主体行为由其分利技术(θ1)和用于保护资源的投入(f)共同决定。
因此,经济状态取决于金融主体与非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金融主体的行为起主导性作用。在经济状态1和经济状态2中,非金融主体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f)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状态;在经济状态3和经济状态4中,非金融主体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f)和分利技术(θ1)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状态。具体来看,整个经济可能呈现如下几种状态(各状态及条件如表 2所示)。
| 局部均衡点 | De(J)的符号 | Tr(J)的符号 | 稳定性 | 条 件 |
| E1(1,0) | + | - | ESS | 0 <θ2 <R(1-β)/[A(1-α)]+αf/(1-α) |
| - | +/- | 鞍点 | 其他条件 | |
| E2(0,0) | + | + | 不稳定 | 任意条件 |
| E3(0,1) | + | - | ESS | βR/(αA)+f <θ2 <(α-θ1)/α+f |
| - | +/- | 鞍点 | 其他条件 | |
| E4(1,1) | + | - | ESS | (α-θ1)/α+f <θ2 <1 |
| - | +/- | 鞍点 | 其他条件 | |
| E5 | +/- | 0 | 鞍点 | 任意条件 |
(1)当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系数(θ2)在区间1时,E1(1,0)为演化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在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给定的前提下,此时社会中非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最终会形成(参与金融化分利,支持生产)的稳定状态;而当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增加时,为保持稳定状态,θ2自然也会提高。如果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给定,那么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将会小于R(1-β)/(αA)+(α-1)θ2/α。显然,如果θ2提高,为保持稳定状态,f自然也会提高。由此可以看到,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和非金融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决定了经济中最后的稳定状态。
(2) 当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系数(θ2)在区间2时,上述各局部均衡点都不是演化稳定点,所以此时没有演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化主体的分利技术(θ2)在这个范围里,社会不会形成演化稳定策略。此时非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可能选择(专注生产,支持生产)的策略,也可能选择其他策略,但不会形成持久的稳定状态。
(3) 当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系数(θ2)在区间3时,E3(0,1)是演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说,在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给定的前提下,此时社会中非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最终会形成(专注生产,从事金融化分利)的稳定状态。而当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增加时,为保持稳定状态,θ2自然也会提高;当非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1)提高时,为保持稳定状态,θ2就会降低。如果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给定,那么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在((αθ2-α+θ1)/α,(αAθ2-βR)/(αA))范围内。因此,无论是θ2或θ1提高,为保持稳定状态,f都会提高。
(4) 当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系数(θ2)在区间4时,E4(1,1)为演化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在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给定的前提下,此时社会中非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最终会形成(参与金融化分利,从事金融化分利)的稳定状态。而当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增加时,为保持稳定状态,θ2自然也会提高;当非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1)提高时,为保持稳定状态,θ2就会降低。如果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给定,那么经济主体为保护生产所支付的资源(f)将大于(αθ2-α+θ1)/α。因此,无论是θ2或θ1提高,为保持稳定状态,f都会提高。
从上述稳定演化策略可以发现,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2)与非金融主体用于保护生产的资源(f)以及非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θ1)密切相关,每一个θ2的取值范围都受到f或者θ1的影响,因此非金融主体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f与金融主体分利行为进行对抗,最终有可能达到某个演化稳定状态。
五、 理解金融化现实:经济关系生成机制及其影响 (一) 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方式及其经济关系资本寻求增殖与积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是维持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资本的增殖与积累是手段,而扩大再生产是目的;但是,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反而将扩大再生产当作手段,把追求资本增殖与积累变成目的。于是,本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变成了资本脱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交换而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增殖的过程,而增殖后的资本将不再投入用以扩大再生产。具体地,可从现实中非金融企业的三个转变来理解其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金融化的。
首先,是企业治理理念的转变。非金融企业的发展目标,从之前强调多元化目标(企业财富、股东价值和社会责任等)逐渐转变为集中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此时,股利分红以及股权出售获利成为企业关注的最主要指标,这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股东价值的增长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减少,从而抑制了生产投资活动;另一方面,为提高股东价值,企业选择增加金融资产和负债,从而助长了金融投机活动。
其次,是企业业务模式的转变。在既定约束下,企业甚至可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以实现盈利,这取决于其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成本之间的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快速增加的金融资产流动性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收益率,多样且便利的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负债成本。此时企业无需生产实际消费品就能获得高利润。
最后,是企业积累结构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使得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在战略决策中设法规避长期的固定资本投资,取而代之的是能在短期获得收益的金融投资。这些生产性的长期固定资本投资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而对金融资产持有量的增加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资本存量。
(二) 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方式及其经济关系人类从最初的简单协作发展到社会分工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经济剩余是促进其交换、消费(劳动力再生产)以及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强化的私有化制度又一次次推动了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直至金融行业从一般商业中独立出来专门从事资本交换活动,为资本的运行开辟了新的渠道。这些渠道形成了经济中的“财富效应”,刺激了消费并引致投资增长,带来了暂时的经济增长,于是各种金融企业都开始尝试这种业务。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其经营对象的转变,从之前的为企业提供发展资金转变为向普通家庭提供各类金融服务,主要目的是拓展其利润来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减少了住房、养老、教育等公共支出,使得普通家庭不得不从银行寻求资金帮助,而且普通家庭的储蓄也被政府引入金融体系,如养老金入股市、个人持股计划等。
二是业务模式的转变,从之前的从事单一存贷业务转变为经营各种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等。一方面,从以贷款获得利息的经营业务调整为以参与各种证券业务获取相关费用为主的业务。商业银行开始利用其创新的衍生工具赚取高额利润,基本上脱离了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本职功能。另一方面,已经金融化的非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从事兼并与收购等非生产性经济活动,而这些投资银行的业务也成为原来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
(三) 普通家庭被动金融化行为及其与其他主体的关系这里的普通家庭是指在社会生产中提供工人以及劳动的家庭。前面没有专门讨论普通家庭,是因为普通家庭的金融化行为是被动的。这种被动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1) 当资本利润率下降时,非金融企业减少了实体投资,金融企业开始设法从普通家庭赚取利润,其后果是普通家庭的债务及金融资产比重不断增加。(2) 普通家庭的失业或工资下降,使其必须透支未来剩余价值以信用贷款的方式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刚性需求,如住房抵押贷款等。这种被动的金融化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普通家庭的收入被纳入金融体系后,将从货币形式变成生息资本或者在资本市场以证券化的方式变成虚拟资本,将不再参与实体经济生产,而是在虚拟经济系统内不断增殖和膨胀,积累金融风险。
其次,当普通家庭被纳入金融体系后,其负债率以及金融资产比重逐渐增加,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成为金融损失的转移对象,将是危机中最后和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普通家庭作为劳动的来源,其被动金融化本质上是在生产领域被剥削一次之后在金融领域又被二次剥削。
(四) 经济主体金融化行为的现实影响根据上述金融化经济关系的生成机制,结合现实的经济背景,可以看到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影响:
首先,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促进了经济主体自身的发展。当从事金融化行为的投资主体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一部分跟随模仿者,这种跟随模仿的策略(羊群行为)容易带来金融动荡和经济风险。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会主动采取改变融资方式的金融化行为来规避这种风险。一方面,新的金融化融资方式通过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将利息、股息和利润等未来才能获得的收入转变成可直接进行交易的资产;另一方面,金融化行为给非金融企业提供新的投资渠道,即除了生产之外还可选择在金融领域进行投资。
其次,金融主体的分利行为与非金融主体的生产行为经常呈现对立的经济关系并容易被激化。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非金融企业与金融企业互相依赖并共同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非金融企业与金融企业经常呈现对立的经济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这种状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企业发达,利用其先进的金融技术分割剩余价值,使得金融的利润率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生产利润率,而非金融企业却因承担创造社会财富的历史责任而举步维艰。
最后,没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必然因非金融企业或金融企业的霸权导致矛盾激化而陷入危机。根据模型分析可知,一旦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化积累了大量剩余价值并熟练掌握了金融技术、渠道以及经营管理经验之后,其分利程度可能会超过金融主体(条件θ1 <θ2与θ1 <(αA-βR)/A不再成立),也可能直接成为金融主体,专注于金融化分利活动,这将直接打破原有的稳定状态,导致金融乃至经济陷入危机状态。
六、 结论与启示本文从经济主体微观行为的角度,利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金融化作用机制的系统分析框架,并分析了现实经济中的金融化现象及其后果。研究表明:首先,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演变推动了全社会的经济金融化乃至金融危机,即非金融企业主要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且试图摆脱银行等金融企业的融资束缚,金融企业则关注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并将普通家庭纳入其体系使之成为新的利润源泉,而普通家庭则被动金融化并被迫接受强势经济主体的二次剥削。其次,经济发展状态取决于金融主体与非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金融主体的行为起主导性作用,非金融主体通过其分利技术和保护行为影响金融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稳定状态。最后,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影响:一是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促进了经济主体自身的发展;二是金融主体的分利行为与非金融主体的生产行为经常呈现对立的经济关系并容易被激化;三是没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必然因非金融企业或金融企业的霸权导致矛盾激化而陷入危机。
因此,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政府应当积极介入并疏导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短期来看,为应对中国当前股票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报酬率以及社会保障来降低普通家庭的投机行为,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创新补贴力度来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投机行为,通过约束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来引导其投资方向,减少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分利行为。长期来看,需要构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按劳分配体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积累的矛盾。
当然,由于本文只是将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演化博弈方法结合起来的初步研究,因此只构建了包含两类经济主体(非金融主体与金融主体)的分析框架。为了使分析框架更具解释力并符合现实,可进一步构建包括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行业组织、居民和政府等五类经济主体的演化博弈框架,并在此多重博弈框架下进行经济金融化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1] |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李安. 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30–58. |
| [2] | 鲁春义. 垄断、金融化与中国行业收入分配差距[J].管理评论,2014(11):48–56. |
| [3] |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
| [4] | 马慎萧. 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解释金融化转型机制的四种研究视角[J].教学与研究,2016(3):71–79. |
| [5] | [德]希法亭.金融资本[M].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 [6] | 肖斌.金融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透视[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
| [7] | Hunt E K. Marx as a social economist: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J].Review of Social Economy,1979,37(3): 275–294. |
| [8] | Jeanneney S G,Kpodar K.Financial development,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poverty[R].CSAE Working Paper No.2005-09,2011. |
| [9] | Krippner G 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M].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
| [10] | Lapavitsas C. Theorizing financialization[J].Work,Employment&Society,2011,25(4): 611–626. |
| [11] | Lazonick W, O'Sullivan M.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J].Economy and Society,2000,29(1): 13–35. |
| [12] | Levine R,Rubinstein Y.Liberty for more: Finance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R].NBER Working Paper No.19380,20l3. |
| [13] | Palley T.Financialization: What is it and why it matters[R].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53,2007. |
 2016, Vol. 42
2016, Vol.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