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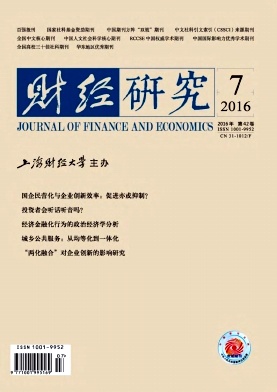 | 财经研究 2016年42卷第7期 |
- 陈旭东, 田国强.
- Chen Xudong, Tian Guoqiang.
- 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思想及其现实镜鉴
- Sima Qian's Economic Thought of Governance by Conven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 财经研究, 2016, 42(7): 63-74
-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6, 42(7): 63-74.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5-11-02
2.上海财经大学 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2.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意义及其与国家的善治、良治有何内在关联,逐渐成为值得研究与挖掘的重要经济学课题。①(①按照制度演变的时间长短,威廉姆森(2000) 将制度划分为:第一层次是“嵌入"的非正式制度;第二层次是正式制度;第三层次是治理制度;第四层次是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按照Davis-North(1971) 的划分方法,制度则可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1962)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习俗做过大量论述,他认为“习俗的势力超过个人,甚至国家”,“现代经济社会没有从习俗变化到契约——它已经从原始的习俗变化到商业的习俗”。②(②引自[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68、373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习俗与市场行为规范之间确已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
Young(1993,1996) 则开创了利用演化博弈论研究制度的先河,他所强调的制度主要就是非正式制度,即一个社会的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其起源与变迁均是在一个稳定的博弈结构中进行的。
其实,早在现代市场经济远未形成的“前现代社会”,习俗就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1987) 曾将非市场经济的典型纯粹经济模式分为两种: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封建制度是两类经济的一种混合类型;而典型的官僚政治则是另一种混合类型,其特征是指令性更强一些。汉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期,习俗在此间及此前的社会经济运行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汉中期,司马迁在其鸿篇巨制《史记》的撰写过程中,曾根据文字记载和实地采风所获得的大量民俗资料来构筑其宏大的历史图景,并在此基础上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阔学术视野,寓论断于序事,提出了一种“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国家治理观,①(①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对管仲执政理念进行评点,认为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全赖管仲之谋,以至管仲死后,“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在对史实的叙述中将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也是«史记»的一大特色。)笔者称之为“因俗以治”。②(②这里借用了我国古代历代政权对边疆民族治理的独特制度概念,更加突出其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治理中的作用.龙登高(2012) 也认为,司马迁的经济论述中有一种理念,即“顺着人的天性与民间的习俗来进行治理,这样才能因势利导,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国家治理,维护社会秩序".引自龙登高:《历史上中国民间经济的自由主义朴素传统》,《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据统计,“俗”字在《史记》中共出现168次,在全书不同篇目、不同语境中互文显义,特别是在专论经济、治生问题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出现了23次之多,司马迁在此篇里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民间各地的不同风俗、习惯及其不同经济后果,可见习俗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其治道思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如此关注习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并不多见。本文的研究显示,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不同侧面,其核心是因循人“生有欲”和“皆为利”的本性及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施事,如此才能达到“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
事实上,学界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如胡寄窗(1963) 、叶世昌(1978) 、赵靖和石世奇(1991) 等的通史性专著中均曾列专节阐述,韦苇(1995) 、朱枝富(1999) 、王毅和刘立(2004) 等则通过专著来系统论述,石世奇(1989) 、刘社建(1996) 等都对司马迁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善因论”作过专文分析,但大多并未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中俗的范畴相关联。张大可(1983) 曾注意到司马迁考察过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张俊(2008) 则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进行了系统探讨。这些研究很有启发性,但均未进一步延展至治理层面来展开论述。与本文的结论相似的是,杜长征(2007) 也认为,至治思想在司马迁整个思想体系中是“统摄性和指引性”的,同时“俗”在其治道思想中也不可忽视;曹应旺(1996) 也对因民之俗与长治久安进行了阐述,但对于习俗在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则认识不足。两者对于俗与治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也均比较薄弱。本文系首次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谱系中“俗”与“治”这两大重要范畴进行关联阐述的专题研究,并将司马迁的治道思想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结合现代经济理论对其进行延伸扩展,探讨其现实意义。
接下来,本文尝试从介绍司马迁“因俗以治”治道思想的源流和主张切入,研究和把握习俗对于建构和优化国家治理模式的作用。人类社会有若干规制经济行为的基本协调机制,包括作为强制性官僚协调机制的政府、作为自利性交易关系总和的市场以及自愿互惠的联合性协调机制或公民社会(雅诺什·科尔奈,1992) 。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应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三大基本要素。①(①虽然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论述并不少见,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单单考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的,在改革的力量博弈和国家的公共治理中还应加入社会一方,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健全的社会才可能支持健全的政府和健全的市场,才能形成良性互动.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强制性的法规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包括习俗在内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从而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并大大节约交易成本。从中短期来看,习俗则是作为既定制度环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范畴而给定的,是政府制定社会经济政策需要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正确理解和认识到习俗既是作为“俗之所欲”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约束,又是可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安排,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到其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中需要考虑的约束条件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政府善治需尊重既有制度环境中的风俗习惯并因势利导,尽量少干预、不干预,而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可以让正式制度安排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兼容,促进经济绩效的提高;社会道德规范的重建则需要借助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让好的习俗成为一种稳态均衡而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
二、 司马迁治道思想的源流:从无为而治到因俗以治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前中期,文化和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百家争鸣走向大一统、大综合的过程,而“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则为司马迁博览文今古文献、②(②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完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③(③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此,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哲学谱系是丰富多元且兼容并蓄的。当然,如果从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评价来看,④(④引自《汉书·司马迁传》。)其父司马谈独褒道家的六家要旨解说应该对司马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后者的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观念有着浓厚的道家哲学基础。
不过,司马迁并非执迷固守的道家信徒,而是对传统道家思想有所批判和扬弃。他在《货殖列传》开篇引《老子》第八十章而斥之,认为那种不用器、不远徙、不乘舟舆、不陈甲兵、结绳而用的“小国寡民”对近世而言无疑等于闭塞民众耳目,已行不通。⑤(⑤当然,也有学者(李埏,1999) 认为,《史记货殖列传》断句应该在“必用此为务”处结束,后句“几无可行”并非指称所引述的老子的观点.参见李埏:《<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初以“无为而治”为中心的“黄老学说”则将消极的道家传统思想改造成了相对积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如Dorn(1998) 所认为的,这里的“无为”已经由不作为演化为不采取违反自然的行为。司马迁对“黄老学说”是非常认同的,这从他对习用“黄老之学”的汉初相国曹参“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⑥(⑥引自《史记·曹相国世家》。)的记载以及对汲黯任地方官“治务在无为而已”⑦(⑦引自《史记·汲郑列传》。)的评述,可见一斑。
其实,“无为而治”并非道家的专利,在儒家的思想源流中也有迹可寻。早在《论语·卫灵公》中,就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叙述。在汉初学术走向融合的大背景下,“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道家“无为”学说基础之上,也融入了儒家“无为”思想的成份,特别是到了后期儒家思想趋于独尊的时期。在老子《道德经》所呈现的图景里,只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使民无知无欲,就可实现“为无为,而无不治”,①(①引自《道德经》第三章。)然而这一治国蓝图过于看重清净无为的一面。儒家的“无为而治”则更注重“治”的一面,且有着相对现实些的目标作为参照系,其最高目标当然是要达到尧舜之治,次优也是要恢复周政。儒家的治国目标在《礼记·礼运》中有一些基本的阐述,孔子所描述的尧舜之治是大同之世,②(②易经对黄帝、尧、舜时期的治理之道概括为“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这其实也是对远古帝王不干涉、因任臣民、无事安逸为政方式的一种肯定。)彼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则是小康之世,人人为己,所以希望通过君主修身而致天下治,靠上行下效的礼来匡正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在司马迁的治道思想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尽管不是唯一的。从《史记》中“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③(③引自《史记·楚元王世家》。)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④引自《史记·酷吏列传》。)等诸多类似评述或引述中可看出,其评价政治兴衰、人物善恶、事务是非的标准基本是依据儒家的价值观点。实际上,司马迁是遵从父愿怀着“承五百年之运、继春秋而纂史”的使命来创作《史记》的,不可避免会受到孔子及儒家史观的影响。司马迁个人的成长也受儒家学风的熏染颇深,十岁便习诵古文,二十岁北渡往齐鲁两地研讨学问,考察孔子遗风,曾问故于孔子后人孔安国,⑤(⑤参见《汉书·儒林传》)也曾向大儒董仲舒习《公羊春秋》。司马迁对孔子也推崇备至,在《孔子世家》篇末曾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史记》的其他篇章也对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给予了大量篇幅,如《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一尊儒倾向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特征是相吻合的。
从孔子的“今大道既隐”⑥(⑥引自《礼记·礼运》。)到司马迁的“俗之渐民久矣”⑦(⑦引自《史记·货殖列传》。),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两者对于现实社会与远古理想社会渐行渐远的类似感叹。那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至治目标呢?⑧(⑧引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⑨(⑨引自《史记·货殖列传》。)其中最理想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听任人民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善因论”是司马迁基于“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针对汉武帝时期“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的现实弊病而提出的朴素的自由放任治理观,⑩(⑩引自《盐铁论·轻重》。)与儒家早期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⑪(⑪引自《论语·尧曰》。)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⑫(⑫马涛(2001) 也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其要义在于对“俗之所欲,因而予之”,给予并保护私人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的自由以为其自身谋利,从而实现民殷国富、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个体自利的现实之下实行“简单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就会内在而有逻辑地达到一个可能不是自利个体本意的结果,实现利己和利他的激励相容与共融,导致社会福利的提升。
三、 因俗以治思想的具体主张:从人性出发立俗施事习俗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增进经济体制效率(Arrow,1971;Young,1996) 。衡量交易成本、决定经济效率则有两个关键要素——激励和信息,这也是机制设计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在Young(1996) 看来,习俗作为一种社会博弈均衡,本身与激励高度相关,正是由于个体没有激励来背离这个均衡,使得习俗具有某种自我维系性和持续性,而不需太多的政府干预与监管,这样就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较好地协调预期和减少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从而大大地节省交易成本,使效率得到改进。亚当·斯密(1972) 也曾谈到习俗的稳定性,指出:“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①(①这里的风俗习惯,对应的就是英文版中的“manners and customs"。引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49页。)
通过对《史记》的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司马迁语境中的“俗”有两层含义:一是一个社会普遍流行的民众心理状态,如“其俗宽缓阔达”;②(②引自《史记·货殖列传》。)二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普遍行为习惯,如“其俗纤俭习事”。③(③引自《史记·货殖列传》。)习俗正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习而成的扎根于民间的社会心理、信念和惯例,它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合作范式等。由于习俗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在中短期内难以发生变化,因此当政者最好能把它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托和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可对前述司马迁的“善因论”有更进一步的解读:在制定政策时,最理想的策略是将习俗作为经济制度环境中的重要因素给定而随俗而动;③(③引自《史记·货殖列传》。)其次是用利益来诱导习俗朝着当政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再次就是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教、教诲;继后则是制定规范,强制性地对习俗进行改造,使之进入当政者所制定的规范之中;最不可取的做法是与习俗针锋相对,强用自己的一套东西来代替习俗的功能,以争利于民。
(一)因俗以治的人性起点:“生有欲”与“皆为利”
欲望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已知条件”,④(④引自[日]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司马迁对欲望也有精辟论断,曾指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⑤(⑤引自《史记·礼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对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限性这一基本经济矛盾的古典阐释。因此,“因其欲然”也就成了司马迁语境中实现止乱达治的必然要求。⑥(⑥引自《史记·律书》。此为司马迁对汉文帝治国之道的评点之语。)那么,“俗之所欲”包括哪些内容呢?司马迁对此有一个高度的凝练概括,他形容“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⑦(⑦引自《史记·货殖列传》。)这些都是人的本能和本性,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限制,它将尽情发挥,追求极致,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永不餍足假设别无二致。
与欲望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利己性。在通常情况下,个体都是逐利的。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进而建构其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设想的伦理前提。无独有偶,司马迁早在2 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②(②引自《史记·货殖列传》。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也曾引用此句:“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盐铁论》毁学第十八)。)这一“皆为利”的假设更是对客观现实的描绘,可与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持守的“经济人”假设相媲美。由此也导致了《货殖列传》中提到的“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和“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的激励相容局面。③(③引自《史记·货殖列传》。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也曾引用此句:“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盐铁论》毁学第十八)。)司马迁形容这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④(④引自《史记·货殖列传》。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也曾引用此句:“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盐铁论》毁学第十八)。)与斯密和哈耶克等的自然、自发秩序观形成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的辉映。
(二)因俗以治的治道方针与治理主张
司马迁认为,良治之道应遵循“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的方针,⑤(⑤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也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评价。)即当政者在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时,应该立足于既有制度环境中习俗惯例的基础上,并随着时间推移、事物变化而发展,如此才能达到“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⑥(⑥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大量历史事件和经济实例进行了剖析和点评,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内含其中的关于因俗以治的若干主张。
第一,不同地区的习俗差异与各自的土地、人口等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反过来又对当地生产生活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此有大量描述。如在“膏壤千里”的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在“地薄人众”的中山地区,“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则是对相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民俗响应。另外,正是由于掌握了中山的民俗特性,又使得温、轵“北贾赵、中山”,促进了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在种、代地区,“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则导致“不事农商”,社会经济畸形运转。
第二,由于不同地区的风俗有所差异,如不顺应当地的习俗,也不因地制宜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采取一刀切的治理策略,则是不合宜的。在《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两个篇目中,司马迁分别介绍了太公望在齐国“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使齐国崛起为大国的故事以及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后强行用周人的礼制来“变其俗,革其礼”而使得“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的故事。在这里,司马迁提出了因俗而简礼与简政的主张,并以归民与近民激励向当政者直陈了这一治理策略的好处。
第三,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单一向度的,有厚薄之分,善恶之分。如果因薄俗、恶俗而治,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反之如能加以适当引导,破除恶俗,树立善俗,则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宁太平,即所谓“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⑦(⑦引自《史记·乐书》。)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了关中地区的风俗从周朝的“好稼穑”到秦朝的“多贾”,再到汉朝的“益玩巧而事末”。这种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自发性演变导致的结果是“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种符合人性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演变不是他所批判的那些主张“制俗”的人就能制得了的,从而需要因时制宜。
第四,在习俗与礼仪制度之间存在转换关系,即所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⑧(⑧引自《史记·礼书》。)也即从非正式制度安排向正式制度安排的转换。司马迁在《礼书》中曾论及“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并对“至矣”之礼进行了阐述,称其要做到“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既富于文采但又有节制,明察秋毫而又不细苛。因此 ,司马迁对于礼制主张采取一种节制的态度。并且,司马迁对于礼制与法制也有所区分,并给出了初步的治理边界。他指出:“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①(①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四、 司马迁治道思想陷于绝响困境之根由司马迁因俗以治的治道思想并未被当世执政者所真正接纳和实施,也不为后世学人所广为传播和扩展,特别是在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治国之道以及班固在《汉书》中对司马迁作出“迹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等批判性评价之后,②(②引自《汉书·司马迁传》。)几成绝响。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挖掘,直至近代才开始有学者进行系统的论述。现今一些学者更是将其地位上升到了与亚当·斯密等相比拟甚至更超前的高度。③(③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包括张维迎、韦森、Leslie Young等.如张维迎(2011) 将司马迁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近代以前这么长的历史时空中得不到重视和采纳呢?原因无非两类:一类是外生性的,一类是内源性的。
自汉武帝开始,空前统一的国家机器就开始极力试图以行政力量干预民间习俗的走向,使之更加符合封建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以确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能够得到有效巩固和延续。这对随后汉朝的民间习俗和官家法律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也是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习俗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模式。作为此模式的肇端,汉武帝时期处于一个从与民休息向与民争利、从无为而治向有为施政的转折期。为了应对因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大举征伐而造成的财政危机,总管国家财政数十年的桑弘羊陆续实行了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与之争”的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使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④(④引自《史记·平准书》。)在桑弘羊为官府广开利孔之后,后世大多所谓贤君良臣也是因循此道而不能罢。
这样,古代社会财产权的确认和分配实际上还是被置于政府的最终实际管控之下,因此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也就难以真正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在因俗以治的治理框架下要实现帕累托效率,恰恰对“俗”的初始条件和市场环境要求较高。按照演化博弈论的观点,习俗被定义为“在有两个以上演化稳定策略的博弈中的一种演化稳定策略”,具有自我维系性(Sugden,1989) 。但是,作为社会经济博弈多重均衡中的某一均衡解,它可能是集体理性的,也可能是集体非理性的,从而不一定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如果初始的习俗条件本身就处于一个集体非理性的均衡点,如何打破这个均衡或实现移风易俗呢?司马迁寄望于礼乐在“善民心”方面的作用,即所谓“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⑤(⑤引自《史记·乐书》。)这大致可以归入“教诲之”的门类,但这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利导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让社会秩序向帕累托有效的稳定状态自发演进。
显然,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包括其因俗以治的治道观)从而也就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实施。尽管我们不应以今日今时的眼光过分苛责于前人,但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包括因俗以治治道思想本身)也有其不足之处或者与社会经济发展有不相适应之处,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和朴素性质,缺乏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的治理边界和适用范围的科学界定。同时,虽然司马迁对许多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俗”与“治”的辩证关系)有独到乃至深刻的见解,散见于《史记》之中,但其经济洞见被淹没在大量的史实叙述之中。如果不加以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就难以使之得到系统化、体系化和立体化的呈现,遑论科学化。相较而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更多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已进入规律和内在逻辑层面的探讨,比司马迁基于史实做出的经验总结更进一层。并且,司马迁依然是站在统治立场来看待经济社会的治理问题,这意味着其所论述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等也仅仅是实现有效统治的工具而已。
五、 因俗以治思想的现代国家治理启示应该来说,经过了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更注重发展的逻辑,而对治理的逻辑没有引起充分重视,使之出现了“成就巨大,但各方面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的这样“两头冒尖”的现象。现代市场制度还远未臻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遑论决定性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政府在“与之争”“整齐之”“教诲之”方面做得较多,而“利导之”“因之”的治理手段则用得不够。这与我们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而持守的全能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理念有很大的关联,政府职能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的定位,政府角色缺位、越位、错位同时存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政府主导干预经济、与民争利、伦理道德滑坡、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关系瓦解等负面特征,无不与此有关,其经济后果就是使得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畸高,经济发展向更高水平的迈进也面临严重阻碍。
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确实非常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治道思想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是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要求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约束条件,包括尊重既有制度环境中的风俗习惯并因势利导,尽量少干预、不干预。否则,反而可能会引起易俗向恶的负面效应。过去一段时期我国房地产市场频繁调控中曾出现的“假离婚”“假结婚”“假社保”等即为例证。政府的很多出于善意的政策设计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不同程度地扰乱了市场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导致经济个体利益调整的紊乱和社会伦理的扭曲,也增加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政府要实现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变,应慎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应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做;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单独或与市场一道发挥作用。同时,在社会领域政府也要有所不为,可以依靠风俗习惯来调整许多法律等正式制度涉及不到或治理成本大的社会生活问题,可以发挥信念、习惯和舆论等的社会自我治理功能。
二是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可以让正式制度安排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兼容,促进经济绩效的提高。市场经济不是人们刻意设计而成的,其本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演进和扩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内含着包括习俗在内的许多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当交易双方在多种约束中选择一种来保证协议的执行时,他们通常也还是会首先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习俗,因为它适合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补充性因素或者一般性交易”。①(①引自张雄:《习俗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随着交易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为了防止非正式制度安排失效,正式制度安排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明确化才应运而生。这种基于市场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才是经济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哈耶克(2000) 也曾借用李约瑟的说法,形容“中华帝国”在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时期,个人的首创精神往往能得到释放,从而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也容易获得巨大进步。无论是制度变迁还是技术进步,经济自由都非常重要。如此看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关于给予并保护私人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自由以为其自身谋利,从而实现民殷国富、长治久安的倡言,依然值得记取。
三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重建。需要借助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让好的习俗成为一种稳态均衡而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诚信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其实质就是一种均衡。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指责的,所以每个人都遵守诚信法则是一个纳什均衡;而在一个人人都尔虞我诈的社会中,谁选择诚实守信则他的利益也必然受损,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这样,恶俗环境下的人人尔虞我诈和良俗环境下的人人讲求诚信都可以是纳什均衡。那么,靠什么来导向信守诺言的好的纳什均衡呢?靠的就是法治和市场激励的双重手段,久而久之就会潜移默化地导俗向善。人们常将公序与良俗并列,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下,好的习俗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好的公共秩序环境。
如前所述,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规制经济行为的三种基本协调机制,而与之相对应,经过强制性的法规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的长期熏染,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无欲则刚”的社会规范、规则意识和价值观,让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好的习俗)作为一种内在规约嵌入社会运行中,将可以对正式制度安排形成有效补充,极大地增强市场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不过,三者中法规治理还是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好的法规治理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反之亦反是。并且,法治的首要意义是人民对天然具有膨胀倾向的政府公权力的限制以确保经济自由,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行为的规约以维护市场竞争。基于此,才能让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产生助益性。这就是法治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习俗在内的文化的社会经济意义也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中,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和谐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当前我国所倡导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其意义倒不只在于文化产业的壮大,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在于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重塑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构建真正的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将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导向正面,带来社会制度环境和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
六、 结论习俗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需要从历史和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智慧。本文以司马迁的治道思想为研究对象,发现其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而其“善因论”的要义正在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强调不采取违反自然的行为而不是不作为。因此,司马迁因俗以治的治道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因循人“生有欲”和“皆为利”的本性及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施事,以达至“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作为司马迁经济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俗以治的治道思想尽管有着一些未能超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在历史上也一度陷于绝响困境,但也有着许多未被中国传统社会所重视和实施的经济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元素,其中不乏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具有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的观点。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扭曲现象与政府的过度干预有很大关系,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治道思想对矫正这一治理困境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启示。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中,中国如何将习俗的自发秩序和市场的自发秩序相互耦合、相互促进,真正做到尊重民众在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遵循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生成及其演化的内在规律,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久而久之让好的习俗成为一种稳态均衡,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良好运行的“润滑剂”,是一个值得更深入研究的课题。当然,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于习俗经济研究的兴起,如何引入和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准确阐述司马迁及中国历史上其他的习俗治理思想,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推进的课题。
*本文还得到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20130303) 的支持。
| [1] | 曹应旺.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92–97. |
| [2] | 杜长征. 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新诠: 宏旨、结构及困境[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2):101–105. |
| [3] |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 [4] | 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中)[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 |
| [5] |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 [6] |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C].北京:中华书局,1988. |
| [7] | 刘社建. "善因论":司马迁的经济理论[J].唐都学刊,1996(3):28–31. |
| [8] | 龙登高. 历史上中国民间经济的自由主义朴素传统[J].思想战线,2012(3):84–91. |
| [9] | 马涛. 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J].河北学刊,2001(1):94–98. |
| [10] | 石世奇. 司马迁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贡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6):66–74. |
| [11] | 田国强, 陈旭东.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5(5):18–27. |
| [12] | 韦森. 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J].中国社会科学,2000(5):39–50. |
| [13] | 韦苇.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 |
| [14] |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 [15] | [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M].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2. |
| [16] | 叶世昌.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 |
| [17] |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 [18] | 张大可.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J].学术月刊,1983(10):38–44. |
| [19] | 张雄. 习俗与市场[J].中国社会科学,1996(5):33–43. |
| [20] | 赵靖, 石世奇.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
| [21] | 朱枝富. 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M].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9 . |
| [22] | Arrow K J.Politic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social effects and externalities[A].Intriligator M.Frontier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C].Amsterdam: North Holland,1971. |
| [23] | Davis L, North D C, Smorodin C.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
| [24] | Dorn J A. China's future: Market socialism or market Taoism?[J].Cato Journal,1998,18(1): 131–146. |
| [25] |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New York: P.F.Collier & Son Company, 1909 . |
| [26] | Sugden R. Spontaneous order[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89,3(4): 85–97. |
| [27] | Young H P.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J].Econometrica,1993,61(1): 57–84. |
| [28] | Young H P. The economics of conven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6,10(2): 105–122. |
| [29] | Young H P.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welfar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8,42(3-5): 821–830. |
| [30] | Young L. The Tao of markets: 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J].Pacific Economic Review,1996,1(2): 137–145. |
| [31] | Williamson O 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looking Ahead[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0,38(3): 595–613. |
 2016, Vol. 42
2016, Vol. 42


